消失的顶层与底层
——都市文学视野中的《失魂记》
作者丨鲁太光(《长篇小说选刊》副主编 文学评论家)
以年龄或代纪作为研究文学活动的切入点,一个显而易见的缺憾是很容易将这一文学活动变为一个无所不能的“筐”,只要年龄合适,所有作家都可以装入这个“筐”里,比如“七零后”这一最近较为吸引眼球的文学概念,好像所有生于1970年至1980年之间的作家,不管他写的是什么,写的怎么样,只要写东西,就可被命名为“七零后”。这样,我们很难将“七零后”作为一文学活动的主体加以观照,因为,这样的命名,缺少文学活动所必须的主体性特征,即相对稳定的共性。
实际上,对中国当代文学略微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七零后”作为一文学口号或文学活动被倡导时,是有相对明确的主体的:自1996年《小说界》推出“70年代以后”栏目,《芙蓉》、《山花》、《作家》、《人民文学》等期刊纷纷跟进,推出类似主题的栏目后,“七零后”就成为一个响亮的文学口号。略加梳理,我们发现,这一文学口号所涵盖的作家主要包括丁天、卫慧、棉棉、杨蔚然、魏微、朱文颖、戴来、金仁顺等。略作追究,我们发现,这些于1990年代中后期闪亮登场的作家,其书写场域主要是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初步确立自己主体性的现代都市,而其写作也主要表达他(她)们对这一现代造物的新奇感以及这一现代造物带来的新的兴奋、恐惧等杂糅情感。这一方面,卫慧、棉棉领军的“身体写作”可谓典型,在以看似率性的文字张扬都市空间中的“身体美学”时,背后涌动的,也不乏恐惧与疼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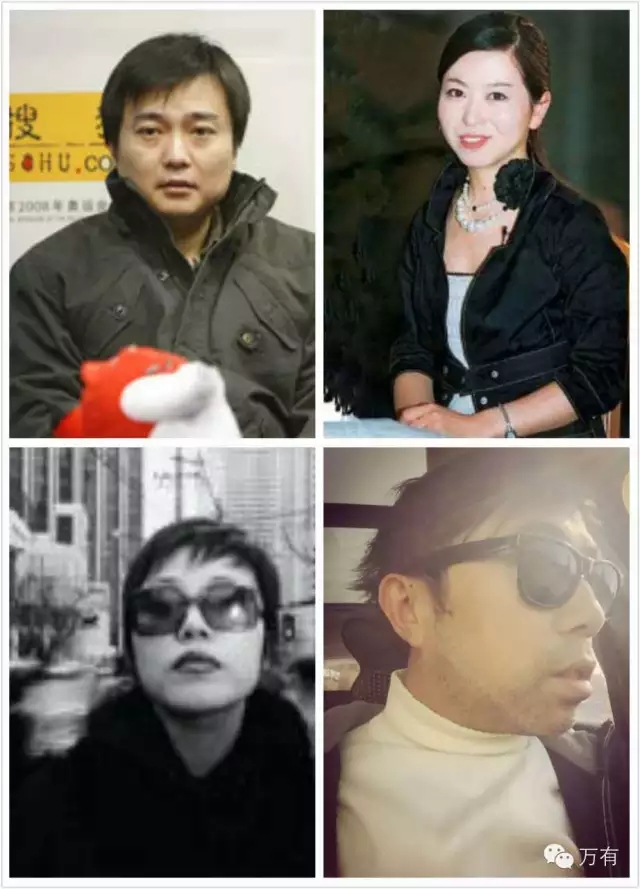
(丁天、卫慧、棉棉、杨蔚然)

( 魏微、朱文颖、戴来、金仁顺 )
由于“七零后”已经成为一个宽泛而暧昧的命名,也由于早期“七零后”作家往往以“都市”作为自己的文学主战场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更由于其时“都市写作”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是一个新生事物,因此,笔者在这里以“都市写作”命名这些早期“七零后”作家,既显示他(她)们与当下“七零后”作家的不同,亦可凸显其文学成就。
对于早期“七零后”的“都市写作”,当时的批评界在对其洋溢的才华、自由的灵魂、率性的文字表达由衷的惊喜之时,也对其写作的无根性,即缺乏历史继承性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现在看来,这种忧虑有点儿“杞忧”之意,因为,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现代都市的确是一个新事物,任何对这个新事物的表述都只能随着时间的延展而发展,而这些早期“七零后”作家,除了一些人逐渐淡出文坛外,也大多在后来的写作实践中以不同方式呈现了“中国都市”的“现在进行时”,尤其在情感——这一“都市写作”最为关键的关键词——方面。
从这条线索上看,我们可以说,杨蔚然在淡出文坛近十年后推出的长篇小说新作《失魂记》,可谓“都市写作”的新发现,或新发展。
这一新发展,首先体现在文风或文体上。
诚如杨蔚然在接受采访时所自陈,在早期创作中,他比较注重作品的先锋性,因而,内容较为飘忽,文风也相应摇摆,但《失魂记》却是一部相对踏实或“写实”的小说。这种感觉,首先来源于这部小说独特的语言风格。阅读中,很容易为作者的语言天赋所折服,因为他能够将各种风格的语言,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语言融为一体,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小说语言。仅就《失魂记》而言,他就征用了雅俗共赏的都市流行语、光怪陆离的网络搞怪语、活色生香的湘楚地方话——特别是长沙方言、声情并茂的电视电影语言……当然,他并不是把这些语言搬来拼贴在一起就完事了,而是经过精心组织,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语言体,制造一种特殊的语言魅力。概言之,是轻松后站着沉重,阳光下涌着黑暗。说句形象的话,他是将“重”放在“轻”上。
不过,语言还只是浅层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说,作者之所以创造这样一种文学语言,是因为要追问一些特殊的问题。离开了这种文学语言,对问题的追问就缺乏应有的力度和深度,即缺乏应有的质量。
那么,作者追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作者追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爱情都去了哪里?
我们在上文中说过,“爱情”是“都市写作”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在《失魂记》中,作者再次正面强攻这个问题。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作者不仅在语言上用功不少,创造了一种寓重于轻的语言,在小说结构上,更是煞费苦心。仅仅翻看一下目录,就会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因为,这个以时间为导引的目录,并非像正常的排列那样,或者倒叙,或者顺叙,或者插叙,而完全是“无序”:一会儿是某年某月,一会儿又跳到另外的年月,而下一部分又是另外的年月,其间差距可逾数年,根本看不出这个变化之中有什么关系——当然,这其中实际上是大有关系的,只是解读这关系,需要耐心。
在阅读中,尤其在初始的阅读中,由目录带来的这种时空错乱感,以及由这种时空错乱感带来的好奇感不仅一点儿也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直到“Chapter 6”,“我”百无聊赖翻看电脑文件无意中发现自己于春风桃花中跟“酒窝女生”的合影时脑海中触电般瞬间一片闪亮而后又一片模糊时,我们才意识到,不是时空错乱了,而是“我”的记忆错乱了,或者说,是“我”的心理时间发生了错乱,而要洞悉这错乱中的真相,就需要将“我”的记忆——心理时间——一一理顺。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个心理开端才是小说叙事的真正开端。也只有从这个心理开端回过头来再次阅读,我们才能进入小说叙述的腹地,才能理解作者的深意:小说名为“失魂记”,那么,何谓“失魂”?
随着这个心理时间的发现,我们看到,那些原本凌乱的物理时间,就像一堆烂牌到了一位高手手中一样,瞬间组合在一起,图像鲜明,层次清晰,似乎具有了生命一般。原来,小说第一章“我”在机场因错拿行李箱而遭遇死婴案,并非意外的惊悚,我因此见到的行李箱的真正主人庄学钟也并非陌生人——其时,他只是以“陌生”面目出现——而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合作者”,而这貌似的“偶遇”里面则包含着无数的精心计算与狠心算计。事情的真相,就藏在这计算与算计之中:2001年3月30日,由于家庭生活失败导致事业失败的“我”,一个人跑到常德桃源的桃花节散心,偶遇八零后美女葛曼丽和莎拉并一起赏花游玩,对葛曼丽心生好感的“我”回到长沙后,经常约会她们,一番追求后,葛曼丽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我”转而追求莎拉,并迅速与之同居,但葛曼丽也并未就此远去,而是沉淀为“我”心底一种难言的爱或痛。其间,我认识了香港商人庄学钟,想借助他东山再起,但一番接触后,庄学钟态度暧昧,几乎出离耐心的“我”,接待时有些破罐破摔了,与其喝茶时把莎拉和葛曼丽也叫来了。“好戏”由此开始:“庄学钟在与葛曼丽握手与对视中,我特别注意到,他闪烁出这几天从未有过的怪异表情。我心稍稍一侧,只有零点几秒。”[1]
这“零点几秒”的“心侧”,将要把葛曼丽引向毁灭。
为了抓住庄学钟这位“贵人”,在第二次接待他时,“我”和女友莎拉做了精心安排:将接风宴安排在葛曼丽和莎拉合租的“家”里。将美女葛曼丽的“私人空间”向“外人”庄学钟敞开的做法,无疑暗示多多,精明的庄学钟自然心知肚明,与“我”心照不宣中达成默契:他投资“我”,助“我”东山再起,“我”负责将葛曼丽推向他的怀抱。
这意味着,对葛曼丽而言,最残酷的时刻虽未到来,但却必将如期而至。就是说,这个故事,在开始时,结果已经一目了然。实际上,这的确没有什么好奇怪和惊讶的,因为,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欲望翻腾的官商两界,这几乎是时刻可能上演的“旧剧”,而非“新戏”。
落入庄学钟金钱打造的窠臼后,葛曼丽也“幸福”了些时日,毕竟,物质的从容对她这样底层出身的女孩是充满了诱惑力的。但就在葛曼丽“幸福”的时候,“我”却再次经历了人生和事业的滑铁卢:2000年4月,“我”狠心抛弃了前妻所生残疾婴孩;2002年11月,就在全香中西餐厅火爆得一发不可收拾之时,弃婴事件爆发,“我一番铺陈之后,这“收买”的一天,这“出卖”的一天,这“牺牲”的一天,这“献祭”的一天,终于来了:在庄学钟投资四百万元后,2001年8月8日,“我”的全香中西餐厅火爆开业,并以日进斗金的状态继续火爆着。12月,到了“我”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在一场精心安排的答谢派对之后,在一场近乎疯狂、近乎堕落、近乎引诱、近乎麻醉的狂欢之后,“我”终于将葛曼丽“送”到庄学钟手中。关于这个情节,作者有一段极其细腻也极其传神的描写:在庄学钟拉葛曼丽去开房之时,葛曼丽是想拒绝的,却没有挣脱庄学钟的掌握,这时,她“就继续看着我,表情停留在一种严肃里。我渐看出眼光要杀人的恶狠”。“我有些慌,眼睛想逃离,但又不行,我明显在接下来几秒有看出了那种‘不是玩笑’和不知为何意的意思”。但“我心态极好地保持着笑,意思是抓下手没什么,接下来也没什么,世界怎样了都没什么,要乖”。但葛曼丽“仍不死心地望着我,口在动,无声,似乎在用口型说着什么”。只有我看到,“我仍笑,说:‘没事,没事,好大个事?’”[2]看这情节,我们知道,葛曼丽几乎是被“我”“送”到庄学钟怀抱中,“送”到庄学钟床上去的,而“我”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抓住庄学钟这位“贵人”,抓住他四百万元的投资。
“我”承认自己喜欢葛曼丽,承认这样做对葛曼丽过于残酷,因而,当葛曼丽落入庄学钟鼓掌中之后,“我”陷入“寒冷”之中,反复琢磨葛曼丽最后那无声的口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突然意识到,葛曼丽冲着我“哦”了下然后又闭合,那形成O型后又收回的双唇,那相碰又张开的口型,想说的不是“火把”,不是“活吧”,不是“混吧”,而是“我怕”。想到这里,我再次看到了葛曼丽“无助的矛盾下的最极端模样”。一念及此,“我猛然一个激灵,像悠然爬行于树干的毛毛虫被针扎了下,疼得激灵”,痛悔自己为什么当时没读出这口型的含义。但瞬间后我就清楚地意识到:“就算我当时看出了、想到了、明白了,又怎样?矛盾后,我仍不会有何毁了计划的打算。我心如铁,近乎六亲不认。”[3]所以如此,无它,只因:“我始终定位明确,商人,狠心,赚得才会狠。我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但愿运气是好的。”[4]
这就是“我”的“信仰”。这也是市场社会的“铁律”。
就这样,葛曼丽被我当做筹码,“送”给了庄学钟。
这是何等的残酷!但这还不是最残酷的,因为“我”深知:“情人只代表情人,只能是从有到无,最高境界也逃不了始乱终弃,只看在哪个时间点上‘弃’。”[5]又是几乎无可更易的“原则”和“基本法”。因而,“乱”虽然残酷,却不是终极残酷。“弃”才是残酷中的残酷。”被知情者王军敲诈,破财消灾失败之后,为了摆脱无休无止的敲诈噩梦,“我”被迫投案自首,陷入牢狱之灾;在庄学钟和律师运作下,我于2003年2月8日缓刑出狱,在这个过程中,庄学钟知道了“我”从他四百万元的投资中“黑”了一百多万的事实,不过,庄学钟不仅一言不发,而且还继续义薄云天地搭救“我”。事实上,这是庄学钟为了让“我”听命于他而给我套上的一条“锁链”——金锁链,而这条“锁链”也牵引着葛曼丽的命运。一番折腾之后,“我”虽然摆脱了牢狱之灾,但由于自己声名狼藉,且元气大伤,餐厅生意一落千丈,“我”不得不于2003年年底注销公司,又开始了游手好闲的日子。
“逍遥”了一段时日,2004年,大约在冬季,逐渐淡出“我”视野的庄学钟再次召唤“我”,因为“弃”的时刻就要到了,他需要“我”去完成这麻烦多多的任务:葛曼丽怀上了庄学钟的孩子,以此要挟庄学钟,要么跟她结婚,要么彻底分手,而这都不是庄学钟想要的结果——他想要的是“玩”,是“游戏”——爱情游戏,因此,他让“我”去帮他说服葛曼丽,解除“游戏”危机。在“我”现身说法的劝告下,葛曼丽放弃自己的要求,打去胎儿,与庄学钟重归于好。为了答谢“我”,也是为了更好地套牢“我”,2005年9月,庄学钟将“我”介绍到湘军天科技公司,经过一番打拼,“我”坐稳了副总的位置,事业和人生再次蓬勃起来。就在这个时候,葛曼丽的终极悲剧时刻到来了:2008年6月,已经从长沙撤得差不多的庄学钟突然再次呼唤“我”,要“我”帮他“了难”,因为葛曼丽再次怀孕,并再次以此为条件要求庄学钟带她去香港结婚,觉得葛曼丽连“游戏价值”也不多了的庄学钟需要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于是再次向“我”“求援”。“我”由于偶然的机缘知道自己的部下阿球在葛曼丽失意之时与之有了一夜情,并疯狂地追求、追寻葛曼丽——一夜情后,葛曼丽觉得无法承受阿球狂热的爱情,于是主动“消失”了——而不得,于是,经过“我”的一番精心安排,当葛曼丽与庄学钟在“老树咖啡”讨价还价时,阿球“偶遇”葛曼丽,并再次向她展开爱情攻势,情势由此急转直下:原本被动招架的庄学钟一下子掌握了主动权,使葛曼丽只能被动“求和”,好不容易才抓住这个机会的庄学钟怎能放弃,于是,一番表演后断然拒绝葛曼丽,满身轻松地返回香港,准备开始新的游戏;葛曼丽由于阿球的突然介入毁坏了自己的计划,羞怒交加中当众羞辱阿球,令其羞怒不堪,为焚毁自己凄惨的生命点燃最后一根火柴。
行文至此,这个悲剧故事的来龙去脉就一目了然,无须赘言了。只需交代一点,即:“我”的“记忆”——心理时间——为什么那么混乱?答案仍然与庄学钟有关,与葛曼丽有关:被庄学钟彻底抛弃后,葛曼丽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与他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就把心思放到孩子身上,想到香港找庄学钟,最后见他一面,请他安排在香港生孩子,好“让崽有个奋斗目标”。在葛曼丽和莎拉一再要求下,或许还有同情与自责在里边,“我”和葛曼丽、莎拉到了香港。2008年7月24日,在驾车追踪庄学钟时,“我”出了车祸,虽然大难不死,但治愈后却留下了选择性失忆的后遗症。这就是“我”的记忆混乱不堪的原因,也是小说叙事时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原因。需要强调的是,这次车祸绝非偶然,而仍是计算或算计的结果。对此,作者有细致交代。在找回记忆的过程中,“我”还原了车祸的真实场面:“此时猛然看到大货近在咫尺,在零点几秒里,我听到的不是脚踩刹车声,而是轰了一脚油门的声音!我的脚明明踩着右边的踏板,我竟然是有意撞上去的!是的,是的,是我自己有意要撞上去的!我是自杀的行为!”[6]
是什么驱使“我”不惜生命危险地这样做,虽然作者没有过多交代,但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却告诉了我们一切:在“我”驾着车就要追上庄学钟的那一刻,就在葛曼丽高喊“快追”的那一刻,就在大货出现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庄学钟的眼睛——他“收回目光的样子像是触到了陌生人”,他“定是要造成没有认出我们的效果”。[7]就是这“收回的目光”让我“惊蠢”了,让我驾车冲向疾驰的大货,因为,庄学钟需要的是“没有认出我们的效果”,是陌路人的效果,而庄学钟之所以能够这样命令“我”,而“我”也之所以这样听命,就在于庄学钟用金钱为“我”打造了一条“锁链”。这“锁链”,辉煌而又沉重!或许,在这生死时速的片刻,我仍然想起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商人,狠心,赚得才会狠。”[8]这“狠”,既指向别人,更指向自己。而这,或许才是“失魂”的真意之所在:在强大的金钱面前,一切都可以抛弃,包括生命,包括魂魄,更不要说什么轻飘飘的爱情和婚姻了。
这就是作者对“爱情都去了哪里”的拷问和回答:在金钱主导的当代社会,对于有权有钱者而言,爱情变成了欲望的对象,消费的对象,一切都不成问题,唯一的问题只在于需要花费的金钱的数量——这在庄学钟那里体现得如此淋漓尽致,为了“消费”葛曼丽,他不仅为其准备了锦衣玉食、香车宝马、华屋丽室、体面工作,而且还“收买”了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爪牙,供自己任意驱遣;对于那些无权无钱的弱者而言,她或他或许需要情感,但在金钱/资本的主导下,她或他却只能放弃这奢侈的愿望,将自己的身体和容貌变成欲望的主体——这在“我”和葛曼丽那里,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对葛曼丽心存爱意,但为了成功,为了赚钱,为了发达,我不仅压制了自己的爱意,而且还亲手将葛曼丽“送”到庄学钟怀抱中去;葛曼丽何尝不如是?她或许对爱情充满着浪漫的憧憬,但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她对庄学钟采取的却是不即不离的态度,而最后委身庄学钟,固然有庄学钟和“我”精心算计的因素在内,但相信她“内心”中是做了反复称量的,要不然,庄学钟和“我”再怎么算计,也不会得逞。而一旦将自己的容颜和身体变成欲望的主体,或者说,一旦将自己交给金钱这个“主人”——这个魔鬼般魔法无边的“主人”,化身为“商品”的“人”几乎就丧失了情感的主动权或选择权,这就是葛曼丽和阿球的故事只能以悲剧结束的唯一原因:原本,阿球和葛曼丽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男的英俊潇洒,女的娇俏美丽,且彼此欣赏,唯一的缺憾就在于阿球缺乏“资本”,而葛曼丽又早已被庄学钟的“资本”所收买,阿球丧失了“再收买”的权利,葛曼丽也没有了再选择的权利。于是,这个原本郎情女貌的故事,就只能演变为血淋淋的奸杀悲剧。
这就是杨蔚然通过长篇小说《失魂记》揭示的现代情感困境。
这个“发现”,无疑重大。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除了作者揭示的这两种“情感-欲望”或“身体-商品”转换模式外,在金钱主导的当代语境中,还有一种“无情”的情感模式——在急速的现代生活节奏和局促的现代生存空间中,被资本/金钱这条狗驱赶得几乎连停下来撒泡尿的时间都没有的现代人,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情感以应对工作,久而久之,就产生了一种“无情”的人生——这就是现代社会“剩男”、“剩女”成为流行语的原因,不是他或她愿意“剩”下,而是现代社会逼迫他或她不得不“剩”下,因为,一旦他或她从工作空间里稍稍停顿下来以在情感的世界里徜徉片刻,等他或她从情感世界中苏醒过来时,迎接他或她的,很可能是原本敞开的工作空间的大门已经紧闭。这是现代人,尤其是现代都市人,面对的更大情感危机。或者说,这个更大的情感危机,是作者揭示的上述两种情感困境的现实背景。
在这个背景下,葛曼丽的人生悲剧,就更加悲怆了。
插一句或许并非“多余的话”:前一段时间,电影《归来》播出后,许多观众为陆焉识和冯婉喻的凄绝“爱情”所感动,直言观影时泪奔不已。实际上,将《归来》(包括其母本长篇小说《陆犯焉识》)当做一个“爱情”故事来接受,是一种双重误读:首先,这是对电影/小说的误读——《归来》/《陆犯焉识》的主旨绝不是谈什么爱情,陆焉识和冯婉喻之间之所以感人的也绝非什么爱情,而是陆焉识的无边忏悔:在年少轻狂时,在青春丽日时,陆焉识何曾把冯婉喻放在心中,跟不要说眼中了,只是随着时日艰难,他才看到了她的“好”,而革命这一暴力事件的突然介入,使他更加意识到她的“好”,于是,在漫长的隔绝中,陆焉识开始对自己的年少轻狂忏悔不已,或许,在这忏悔中,陆焉识产生了幻觉,觉得自己的忏悔就是对冯婉喻的真爱,观众或读者也被这幻觉迷惑了,觉得这就是真爱,但我们可以试问一下,如果这就是真爱的话,那么,什么人能承受这样的爱呢?——有条件相爱时,做的是侮辱与抛弃的事情,没有条件相爱时,却又念念不忘对方的“好”,这是怎样“功利主义”的爱与情啊。那么,导演或作者为什么将“忏悔录”导演/写成“爱情书”呢?这就涉及到导演或作者的本意了——张艺谋和严歌苓不过是借这个“哭诉”的所谓“爱情”故事行“控诉”之实,“控诉”革命对他们的剥夺,对他们轻狂爱情的剥夺,对他们可以始乱终弃特权的剥夺,对他们一切特权的剥夺,因而,这部电影/小说还是典型的“伤痕文学”的路数,里边的所谓“爱情”,不过是一个圈套,而政治,才是真正的旨归所在。
其次,这是对“革命”的误读,准确地说,是对“革命时期爱情”的误读。革命自然有其不堪直视之处,但“爱情”却不仅不是革命时期的短板,甚至可能是其长处——如果对电影《归来》和小说《陆犯焉识》做深度解读,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革命(革命的暴力隔绝与改造)首先恢复了陆焉识的反思意识,而后又进一步恢复了他的爱情意识。只有从这个角度看,陆焉识的“忏悔录”才能解读为“爱情书”。
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双重误读呢?
如果做一点症候式研究的话,答案很清楚:这样的误读是“移情”的后果,是观众或读者把自身的情感状况——极度匮乏——投射到历史中去的后果,而这样的“移情”更严重的后果是使观众或读者进一步遗忘自身的“疾病”,从而更进一步,遗忘自己时代的“疾病”。这样的“遗忘”,看似实现了自我救赎,可实际上,却是更深度的陷落。
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失魂记》的意义才能真正凸显出来:与众人沉浸在自身的“疾病”中而不自觉不同,通过对“爱情都去了哪里”这个问题的执着追问,杨蔚然准确地揭示了我们时代的“疾病”——物质相对丰腴,情感极端匮乏。这堪称“都市文学”的新发现。
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因为《失魂记》在纵向上实现了对“都市写作”的超越——看看葛曼丽的人生悲剧,我们会发现卫慧《上海宝贝》中的“身体叙事”是多么的轻飘与无力,当年,“身体”还可以是“叛逆”的展示,还可以是“解放”的力量,而现在,在都市终于具有了自己吞噬一切的魔力之后,一切“叛逆”和“解放”都是徒劳。当然,《失魂记》在横向上也实现了对“都市写作”的超越,或者说,杨蔚然之所以在纵向上实现了对“都市写作”的超越,在于他首先实现了对“都市写作”的横向超越。我们注意到,杨蔚然将小说的发生地放置在长沙——中国都市的一个独特样板。在一个访谈中,杨蔚然解读了长沙的独特之处:长沙是内陆城市,不是沿海城市,不在改革开放前沿,但在“一切向前/钱看”的时代氛围中,它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都市品格——靠“电视湘军”,靠“超级女声”,靠选秀节目,靠“注意力经济”,长沙在“注意力”方面,在“娱乐领导力”方面,在“眼球经济”方面,不仅早已跻身一线城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重要的是,这种独特的都市文化或都市品格,在为自己营造了一种“天上人间”般的梦幻色彩之时,更为自己打造了一种“人间地狱”的冷血精神,而且,这种笼着梦幻色彩的冷血精神在一种大众文化氛围中,早已在“寻常百姓”心中生根发芽。关于这一点,杨蔚然在小说中有委婉而犀利的揭示——小说中时常出现的诸如“中国演艺航母”等大众娱乐场所及其中上演的句句不离钱色的节目就是一个很好的暗示,而小说中湖南搞笑天王李清德在脱口秀节目中对金钱赤裸裸的崇拜言辞,更是将1990年代“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万万不能”的“拜金口号”远远甩在身后。这才是葛曼丽悲剧的真正根源——我们所生活的都市,早已是一个不再讲感情的都市了,甚至也不再是一个讲欲望的都市了,一切都变成了商品,一切都变成了“鱼肉”,一切都变成了消费。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沉迷于情与欲“都市写作”,已然远离了现实,也远离了真实。
这正是当下“都市文学”的病灶之一。
“都市文学”是这两年的文学热点之一,或者说,是文学界召唤的热点之一。但在笔者看来,“都市文学”的缺点之一就在于对都市情感的呈现。并不是没有相应的书写,也不是相应的书写少,而是书写乏力,没有找出都市情感的真问题在哪里,从而没有找到“都市文学”真正的文学性在哪里。而这,无疑正是《失魂记》的优势之所在。
更重要的是,杨蔚然首次直面了一个特殊的都市人群的生存状态——不要误会了,这个“特殊者”不是葛曼丽,也不是“我”,而是庄学钟。“我”和葛曼丽不过是庄学钟这根藤上结出的两颗苦瓜而已。
1990年代末,当“中产阶级”还没有受到现实的挤压因而生活还相对滋润时,“中产积极”一度成为社会热词,“中产阶级社会”也一度成为一些学者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期望之一。大约就在这个时期,许多都市白领乃至“灰领”都特别喜欢阅读一本叫《格调》的书,期望从中学得些许“中产阶级”生活品味,提升进入这个阶层的软实力。实际上,这并不是一本论“中产阶级”个人修养的书,而是一本硬邦邦的书,是一本讨论阶级/阶层的书,是一本讨论阶级/阶层分化的书——许多“读书人”都忘了读这本书的副标题: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在作者那里,“生活品味”是“社会等级”的从属语,而非关键词。
在“白领”“蜗居”、“灰领”“蚁族”的今天,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了保罗·福塞尔这本书的坚硬之处。保罗·福塞尔指出,除了大街上常见的芸芸众生外,在现代美国社会,还存在着两个“看不见的阶层”:一个是“看不见的底层”,另一个则是“看不见的顶层”。虽然都“看不见”,但“看不见”的原因却截然不同:“底层”是被生活的重压压到尘埃中去了,因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们“只会短暂地出现在某事某地,比如春天的纽约街头,嘴里一边咕哝着自己倔强的幻想。这个一年一度的仪式性自我展示结束后,他们就会再次销声匿迹”。[9]“看不见的顶层”则是被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吓坏了,从那以后,这些“巨富”“在炫耀自己的财产时变得‘谨慎,几乎一言不发’”。与之相应,“大批财富从一些很能鼓励表现癖的地方(比如纽约上城第五大道的豪宅),转到了弗吉尼亚的小城镇、纽约州北部的乡村、康涅狄格州、长岛和新泽西州”。“不仅豪宅被藏了起来,‘看不见的顶层’的成员们也纷纷从他人的窥视和探查里消失了。这一等级的人们往往会极力避开社会学家、民意测验者,以及消费调查人员们详尽的提问和计算。无人对这个等级做过细致研究,因为他们的确看不见。”[10]概言之,这个“看不见的顶层”是一些巨富,经历了19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这个“曾经喜欢炫耀和挥霍”的阶层,“在媒体和大众的嫉恨、慈善机构募捐者的追逐下销声匿迹了。”[11]
虽然这是保罗·福塞尔对1980年代美国社会状况的描摹,但整体而言,这种状况也适合今日之中国社会,就这个“看不见的顶层”而言,这种描摹,尤其重要——经过三十多年市场经济的发急速展,中国社会在经历急剧分化之后,我们社会的“顶层”的确“看不见”了,虽然他们还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及其走向。因而,如何呈现这个“看不见的顶层”,将我们的社会“还原”为一个完整的版块,是人文社科学界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为,非如此,我们就无法准确的认识自身,也就无法看清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就文学而言,尤其是都市文学而言,经过新世纪以来的发展,我们对都市饮食男奴的日常生活景象,有了足够多的书写和呈现;得益于“底层文学”的横空出世,我们对那些为生活重压压到尘埃以下的“底层”,也有了相当多的书写和呈现,虽然这书写和呈现还远远不够。唯一遗憾的是,我们的“都市文学”对这个“看不见的顶层”鲜有触及——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杨蔚然《失魂记》中的庄学钟是我们的“都市文学”中第一个“看不见的顶层”。更为重要的是,关于这个“看不见的顶层”,我们的大众传媒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给了他们大量的赞美之词——主要是他们经济生活中的“荣耀”,而对于他们生活中的阴暗面乃至黑暗面——主要是情感生活中的“疾病”,却很少触及。而这,自然是不均衡的,也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因为,就像他们的“荣耀”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荣耀”一样,他们的“疾病”也往往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疾病”,也就是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象征,至少是极其重要的象征。在这个维度上,杨蔚然《失魂记》对庄学钟这个文学人物的塑造更为重要,他为我们的“都市文学”画廊里增添了一个典型——“看不见的顶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失魂记》是都市文学的新发现。
而我们,自然期望这样的新发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
2015年2月28日 初稿
2015年4月05日 修改
[1] 杨蔚然:《失魂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115页。
[2] 杨蔚然:《失魂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169页。
[3] 杨蔚然:《失魂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170页。
[4] 杨蔚然:《失魂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171页。
[5] 杨蔚然:《失魂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257页。
[6] 杨蔚然:《失魂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97页。
[7] 杨蔚然:《失魂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96页。
[8] 杨蔚然:《失魂记》,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第171页。
[9] 保罗·福塞尔著;梁丽真乐涛石涛译:《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修订第3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年12月第1版,第29页。
[10] 保罗·福塞尔著;梁丽真乐涛石涛译:《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修订第3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年12月第1版,第28-29页。
[11] 保罗·福塞尔著;梁丽真乐涛石涛译:《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修订第3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1年12月第1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