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大帝(下)
作者丨杨友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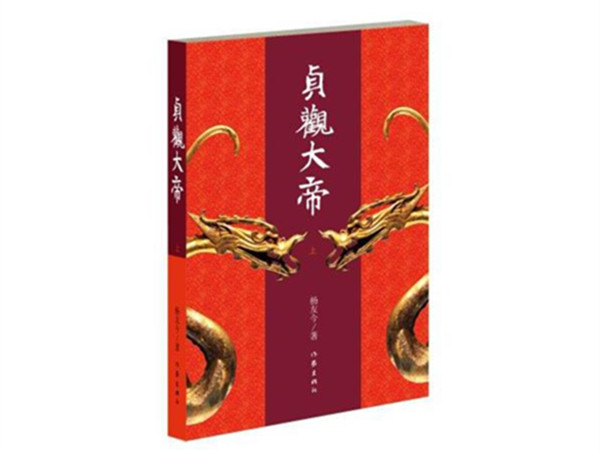
第二十八章 人生感意气
几次接触之后,魏徵也觉得太子并非朽木不可雕也,只要循循善诱,让他走上正道,自强自立,可以承续皇统,成为一代有作为的新君。他回想起承乾八岁被册立当太子时的情景,那么活泼可爱,弥漫着稚气的大眼睛滴溜儿转着,直如两颗熠熠闪光的黑珍珠。浅浅一笑,面容恰似花一样开放,那么甜蜜、纯朴、神采飞扬,宛然象征着未来的辉煌灿烂。高祖驾崩,今上服丧期间,太子代替父皇处理国政,再一次展示了他的聪明和才干。“看来太子放荡不羁不是秉性所为,而是受魏王干扰,自信心不足而产生的后遗症。只要今上不偏向于魏王,太子摆正自己的位置,很有可能恢复被扭曲的心态,走上正道。”魏徵这样想着,好似天风吹开云雾,心境豁然开朗,周身热乎乎的,脸上也绽出了些许欣慰的笑容。
承乾的转变也给李世民带来了一片光明,他满心舒展,公开对文武官员说:“外面传言太子的脚有毛病,走动不便,而魏王聪颖悟性高,又时常伴驾游幸,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开始揣度朕意,捕风捉影,追潮赶浪。要知道,太子的脚虽有病,但并不妨碍行走。《礼记》中说: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的儿子象已经五岁了,朕终究不会以庶子取代嫡子,开启夺嫡的祸源。”
群臣听罢,高兴得手舞足蹈,山呼万岁,声振殿宇,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魏徵辅佐太子承乾,果然产生了神奇的效应,一下便挽回了夺嗣换宗的局面。可是,天不假年,郑文贞公、太子太师魏徵的病情急转直下,李世民接连不断派人前去慰问,赏赐药饵,奔走在路上的车马往来不绝,又派中郎将李安俨住在魏徵家里,随时奏报魏徵病情的变化。魏徵弥留之际,李世民率太子承乾等驾幸魏府,至病榻前攥住魏徵的手,说:
“爱卿,你不能离开朕,一定要把病治好。”
“臣舍不得离开陛下,然而大限已经到了,神仙也救不了我的命啦。”魏徵唏嘘啜泣,眼泪与鼻涕流湿了衣襟。
“卿家有什么话,尽管对朕说。”
“臣一生坎坷,晚年幸遇英主,得以寿终正寝,心已满足,别无他求,惟愿陛下龙体安康,坚持嫡长继承制,不再动摇。”
李世民受了感动,眼圈也红了,用手指着衡山公主说:“朕欲将小女许配给贵公子叔玉,无忌和太子可为媒妁。”
魏徵感动得张开了嘴:“叔玉,赶快谢恩。”
“臣谢皇上隆恩。”魏叔玉当即跪到李世民的膝下,行了叩拜大礼。
“贤婿平身。”李世民温言软语地说,“你和太子既为兄弟,朕就让你留在太子左右,减轻你父亲的劳累。”
魏徵胸脯一起一伏,完全沉浸在激情里,心满意足地阖上眼皮,与世长辞了,时维贞观十七年正月十七日。行年六十四岁。
李世民诏命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全都参加葬礼,并赐予手持羽毛的仪仗和宫廷鼓吹班送葬,陪葬昭陵。魏徵的夫人裴氏推辞说:“亡夫平生节俭朴素,而今用正一品高官安葬时才可以使用的羽葆仪仗,不是他的意愿。”坚持不受,而只用有篷盖围幛的灵车,装载灵柩出殡。李世民登上禁苑西门门楼,遥望上山的灵车,痛哭流涕。他亲自撰写了碑文,表彰魏徵的功德。“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魏徵《述怀》诗中的两句话,正好成了他一生的写照。李世民难忘魏徵,常常登高远眺西北的九嵕山,寄托自己的哀思。他常常用深切怀念的心情和诚挚的语气对身边的大臣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逝世,朕失去了一面镜子。”
“魏徵忠勤可嘉,”长孙无忌宽解道,“皇上给予他的荣耀,也已经高到了极限,倘若他地下有知,应该含笑九泉了。”
房玄龄、高士廉、唐俭、马周和褚遂良等也一齐上前相劝,才止住李世民的悲伤。思前顾后的李世民决计将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图像画在凌烟阁,以资纪念,并供后人瞻仰。他们分别是:
赵公长孙无忌、赵郡王李孝恭(已故)、莱公杜如晦(已故)、郑公魏徵(已故)、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公段志玄(已故)、夔公刘弘基、蒋公屈突通(已故)、郧公殷开山(已故)、谯公柴绍(已故)、邳公长孙顺德(已故)、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公张公谨(已故)、卢公程知节(又名咬金)、文懿公虞世南(已故)、渝公刘政会(已故)、莒公唐俭、英公李世责力、胡公秦叔宝。
李世民的举措,好比给出生入死创立大唐王朝的功勋卓著的文武大臣竖起了一座丰碑。它既没有忘记过去,又展现了美好的未来,激励后人继承他们的意愿与遗志,为国建功立业,争取图画于凌烟阁的最高荣誉。凌烟阁绘制功臣像,同时也说明了唐朝的政权业已巩固,以人与人的结合所形成的政治体制的时代从此结束,新的贵族政治体制逐渐形成。此后要想跻身朝堂,尤其是想成为出人头地的显贵,不但必须惨淡经营,更需要出身门阀的背景。光有真才实学还不够,做官还得五官端正、仪表堂堂,高宗朝的钟馗,考取了进士,其貌不扬,皇榜上便没有他的名字,只能饮恨终身。
凌烟阁矗立在太极宫的东北部,甘露殿以东、神龙殿的背后。阁内的功臣像,是画在各室的白壁上的,亦即壁画,皆出自当时大画家阎立本之手,很为时人所称颂,每一幅图像旁边还题有赞词。后来李世民特意登凌烟阁,观魏徵画像,赋诗祭悼,以志哀思。其诗云:
望望情何极,
浪浪泪空泫。
无复昔时人,
芳春共谁遣?
魏徵的死,恰好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他的死,也引起了朝廷上下的震动,当然,受震最厉害的首推太子承乾。他刚刚鼓起来的一点劲头,一下子又撒了气,那双灰黄的眼珠子失神地望着终南山披雪的山峰,脸上如同挂了霜一般,心头笼着一层乌云,空虚和压抑的感觉在他周围扩展,包围了他,吞噬了他,甚至想到了死。万念俱灰的承乾喝得醉醺醺的,对身边的人说:“我假装是可汗,不幸翘了辫子,你们仿效突厥的风俗,来操办丧事。”说罢,身子一倒,像死人一样僵卧在地上。众人一起放声哭喊,骑上马环绕着“尸体”奔走,然后贴近他,用刀划他的脸。隔了一阵,承乾霍然坐起来,煞有介事地说:
“我一旦拥有了天下,当率数万骑军,到金城以西狩猎,玩个痛快,满载而归,然后解开发髻做突厥人,投靠史思摩可汗,假如给我一个将军的职务,举着马刀冲锋,决不会落到别人的后面。”
“承乾,”李元昌从马和人的缝隙中钻了出来,“你真会玩,玩得多开心。”
“呃,元昌,我正要找你。道士带来了没有?”
“早来啦。不好打扰你的雅兴,安排他们在集贤馆歇着。”
“叫什么名儿来着?”承乾弯曲着手指敲打自己的额头。
“贵人多忘事,只怕就是指你这号人。”
“快告诉我,少啰嗦。”
“一个叫做秦英,一个叫做韦灵符,他们道术高深,还有魔法。嘻,乐童称心也来了。”
“走,走,一起见他们去。”
承乾和他们一见如故,没日没夜地搅和在一起厮混,变着法子取乐。秦英和韦灵符献房中春药,传授房中秘术,承乾欲火如焚,不能尽性,像着了魔一样迷上了称心,跟他同吃同住同睡觉。称心年纪十七八岁,姿容赛如少女一般姣好秀逸,能歌善舞,而且独精淫术,承乾又染上了鸡奸的恶习,再也无法和他分开了。李世民得到消息,气得七窍生烟,两肺直炸,将秦英、韦灵符和称心等人统统抓起来杀掉了,受牵连被斩首的还有好几个人。承乾疑心是李泰告发的,怨恨更深,酷似火上浇油。
李世民愈来愈不喜欢承乾,承乾也明白父皇还在生他的气,横了心,干脆声称有病,不进宫朝觐。他瞞着父皇,私自豢养刺客纥干承基,又雇用了一百多名杀手,先下手为强,决计行刺魏王泰,挖掉这个毒瘤、魔根,彻底消除祸患。
二更过后,甘露殿庭院中静悄悄的,只有李世民和夜值的宫女太监们还没有就寝,整个太极宫显得异常的宁静,仅仅每隔一阵从东西长街传过来打更的梆声,音节单调,催人入睡。李世民坐在西暖阁批阅文书,他时常微微仰起面孔,对着灯光凝神思考,很少留意到院外的敲梆声。一名近侍踮着脚尖走到御案前,低声提醒说:
“夜深啦,请皇上安歇。”
李世民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奏折,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近侍又重复了一遍,他才把手中的朱笔搁到玛瑙笔架上,揉了揉发胀的眼睛,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手脚。甜食房的太监送来了一碗八宝燕窝粥,由当班的武媚奉到食案上,李世民吃完燕窝粥,走出大殿,在丹墀上来回踱着方步。春寒料峭,寒意犹浓,夜空的星斗直若怕冷似的稀疏地点缀在幽蓝的天幕上,如同打颤一样闪闪烁烁。风吹得树梢飒飒地响,大地像被薄纱披盖着,静夜与宫殿悄然并卧于星月之下。他款步走下丹陛,在庭院中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无意识地走到甘露门,恰巧刻漏房的一名太监手提灯笼,抱着时辰牌走了进来。瞧见皇上站在门口,连忙跪倒行礼。
“什么时辰啦?”李世民随口问道。
“回皇上的话,已交子时了。”
太监回完话,站立起来,换下时辰牌子,从原路返回刻漏房去了。
李世民有些困意,但又不想睡,又走进了西暖阁。刚拿起一本奏折准备省阅,大、小杨妃同时来了。行礼后,小杨妃瞅了李世民一眼,关切地说:
“皇上,怎么还不安歇?是不是还在想太子的事?”
“唉,”李世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朕太粗心大意咯;不过,也万没料到太子那么不争气,变得那么坏。自贞观以来,朕自负治理国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然而却没有让太子健康地成长起来,真是愈想愈难过,愧对祖先,愧对社稷,愧对长孙皇后,愧对天下臣民。”
“臣妾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杨妃主动把担子往自己的肩上搁,想减轻李世民的痛苦。“长孙皇后临终托付臣妾,对太子要严加管教,鼓励他进取向上,而我连他滑坡也没有遏止住,让他走上了歧路。”
“他自己不学好,怪不得你们。你们也算费尽了心血,一次又一次地去东宫,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感到厌烦。父母生得了他的身,却生不了他的心。人要好伴,树要好林,怪只怪他身边那些不三不四的败类,恶习感染了他,朕下狠心来了个一网打尽,想必会有些转变。丑话说在前头,他要是再不改过自新,那可就怪不得朕喽。”
“储君乃国之根本,动摇不得,皇上千万不可灰心。”
“朕的身体已大不如从前了,在生之日不解决好储君的事,国家很有可能就会毁在下一代的手里。”
李世民的话还没说完,内妓念奴怀抱琵琶走进了殿内。唐朝建国初年,便在宫中设置了内教坊,管理娱乐性俗乐歌舞,隶属于宫中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构太常寺。教坊中的乐妓,依其在色、艺上的高低以及服务对象的身份,分成不同的等级。专为皇帝表演的,称呼“内人”,身上佩有皇帝赐给的“鱼形袋”。常伴随在皇帝身边的,叫做“内妓”,在容貌、技艺上又胜过一般的“内人”。念奴不仅貌美聪慧,并且才艺甚高,琵琶弹得出神入化,还能根据旧调自创自编新歌曲。李世民爱听她演奏的琵琶,让她早晚不离左右,非常受宠。
“深更半夜的,你来干吗?”李世民带着嬉戏的口气问道,霎时松开了眉头,脸上绽出来一丝笑纹。
“奴婢望见殿内还亮着灯,怕皇上操劳过度,又怕皇上寂寞,特意前来侍候。”
“有二位爱妃作陪,朕一点儿也不寂寞。”
机灵的念奴赶紧朝大、小杨妃福了福:“奴婢拜见二位娘娘,望娘娘恕奴婢的冒昧之罪。”
“免礼,免礼。”二位杨妃把脸转向李世民:“她敢莫就是念奴?闻名不如见面,唷,孩子倒是挺灵巧的,逗人喜爱。”
“让她弹一曲琵琶给你们听听,如何?”李世民颇有兴致地问。
“夜深啦,皇上早点儿歇息,改日再听呗。”
李世民打了个哈欠:“你们都回去,朕也倦啦,再过两个多时辰就得上早朝。”
送走大、小杨妃和念奴,李世民走到大殿背后的温馨房,在武媚和两名宫女的服侍下脱了袍服,上了御榻,可是辗转反侧睡不着,又重新披衣下床,吩咐武媚去把没有看过的一叠文书都搂到寝房来。当重新开始批阅文书时,他叫武媚和伺候他的宫女、太监都去歇息。夜值的宫女们随武媚退到温馨房披檐旁的养荣轩中坐地休憩,等待皇上随时召唤。太监中只留下两人,其余都回到甘露门左右的值房里去了。留下的两名太监睡在温馨房外间的绳床上,和衣躺进貂囊里面,不敢深睡,一旦有事,要随喊随动。
下弦月升上来了,星星稀疏而黯淡,清晖四射的星月装饰着缥缈的夜空,也装饰着沉寂的皇宫。甘露殿外殿的灯火朦朦胧胧,内殿的寝房却异常明亮。窗外恍然用素纱蒙着一般,迷迷茫茫,周围静极了,只有树叶儿被风吹着,发出微弱的簌簌声,仿佛催人入睡似的。伏案阅览文书奏章的李世民仍然没睡意。他一眯上眼皮,就有许多人影晃动,时而是长孙皇后,时而是太子承乾,时而是青雀,时而是魏徵,还有雉奴、武媚。他们交替出现,混混沌沌,模模糊糊,迷离恍惚,犹如梦幻一般,然而又显得那么真切。他拧着眉头,张开鼻孔呼吸,想把占据着他灵魂的阴影驱逐出去,可是它们却不断地闪动着,带着强占性地萦绕不去,愈恼火,愈烦躁,愈跳闪得厉害。
浅灰色的天空透出些许绯红,西北角上浮着的几颗晨星失去了光彩。青白的曙光和淡淡的晨雾交融到了一起,皇宫的轮廓影影绰绰地显露出来。李世民伸了个懒腰,揉揉困乏发酸的眼睛,准备去梳洗房梳洗,他通宵未眠,一直想着太子的事,力求挽救太子,尤其要防止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太子干阴谋勾当。但是,防不胜防,搞阴谋诡计的大有人在,其时元昌正在同母妃密谈。他决计不顾一切地豁出去,跟李世民展开一场殊死的较量,直到取代他的皇位。
听到称心等人被处死的消息,尹德妃慌得浑身发怵,额头冰凉,生怕灾祸蔓延到元昌的身上。她两眼直勾勾地凝视着元昌那阴冷的刀削脸,提心吊胆地说:
“儿啊,你就听娘一句话,最好到梁州任上去,呆在京城没有好处。”
“母妃,你害怕了。是不是?”元昌额头上皱起几条不规则的抬头纹。
“今上精明强干,当年玄武门事变,连大郎和三胡都惨死在他的手上,你们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哩。”
“他们是明争,我却是暗斗。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只要他中我一箭,可就完啦。把他逼下位,我再取承乾而代之。”
“人算不如天算,你想得倒挺美,可就怕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别瞎操心,等着瞧吧,到时候你再看儿臣的手段。”
“你要干吗?”尹德妃满头雾水,弄不清元昌的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元昌诡诈地眨了眨眼睛:“利用称心这个牺牲品,激怒承乾,怂恿他谋反。”
“没有兵权,如何反得起来?”
“侯君集和今上产生了隔阂,心怀怨叛,他女婿贺兰楚石把他拉过来了。”
“此人将略非凡,带兵打仗,还没有过失败的记录。”
“还有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从前是隐太子建成兄的僚属,玄武门事变时,隐太子中箭身亡,他仍拼命死战。今上赏识他忠勇可嘉,命他负责宫城的安全。哪知他怀恨在心,主动投靠了太子承乾,今上的一举一动,他随时在暗中禀报太子。”
“噢,想不到你们联络了许多人,准备倒是挺充分的。”
“如今万事齐备,就只等东风喽。”
“你一说,我悬着的心可就放下来了。”
“母妃,我马上要去东宫,还有要紧的事商量。”
李元昌匆匆走出了大安宫,乘坐马轿,朝东宫急驰而去。
称心被处死后,承乾一直念念不忘,深陷于痛苦和怀念中不能自拔,他把称心的尸体埋葬在东宫后花园内,筑土堆成一座坟墓,私下追赠官爵,树立墓碑,每天他都要去那里转一转,看一看,涕泪交流,踯躅顾盼,久久不肯离开。临近黄昏,他又来到了东宫最北端的承恩殿,他曾和称心朝夕相处,度过了无数个温柔缠绵之夜的寝房,如今改变成了“幽会”室,在室内竖起了称心的塑像,和真人一般大小,给它穿上称心生前所穿的衣裳,梳妆打扮跟活人一样。称心的遗物也都保存了下来,照样放在原来的位置上。承乾进入“幽会”室,首先浏览了一下称心的遗物,然后就在他的塑像前焚香化纸祭奠,拥抱着塑像柔肠百转,翻来覆去地跟“他”亲热,一壁厢诉说心曲:
“称心呀,你不能离开我,一定要留下来,永远和我在一起。没有你陪伴,我会活不下去。你还记得我俩的誓言吗?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可恨父皇偏不成全我们,残忍地杀了你。我好伤心的,心如刀割,愁肠寸断,简直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心肝哇,你知道是谁害死你的吗?就是那人面兽心的青雀,是他告的密。他想夺取我的太子座位,想用他的优势比垮我,处处算计我,不幸让你当了替死鬼,惨遭不测。”
他哭一回,诉说一回,再哭一回,再诉说一回,音调凄切哀惋,一边用双拳猛捶脑袋,浑如一头被迫窘了的野兽,随时准备伺机反噬。
“有仇不报非君子,有恩不报是小人。我要报仇,我要报仇,我要杀死青雀,杀死他,杀死他,杀死那个狼子野心的家伙,杀死那个卑鄙龌龊的小人。”
“殿下,你在胡说些什么?隔墙有耳,说话留神点儿,少惹麻烦。”
太子妃躲在门边偷听偷看了一气,实在忍耐不住了,跨进门槛,进行劝解。太子承乾由于受了严重的刺激,加之过度的哀怨和忧愤,神志有些不清醒了,恍恍惚惚,沉迷到了和称心的“幽会”中,对于太子妃的干扰和打岔,异常气恼,恼羞成怒,一股无名火从心中窜起,托地跳将起来,一脚踢到了太子妃的软肋上。太子妃倒退了好几步,倒在门旁边,承乾上前抓住她的发髻,把她提起来,左右开弓,扇了好几个耳光。他一边打一边破口骂道:
“谁叫你来的?你吃什么醋?我早就说过,只要称心和我相伴相随,不要你们了。”
“太子,”太子妃好不容易挣脱出来,“你下死手打人,我劝你不应该吗?称心已经死了,你怎么还不振作起来?”
“我振作起来有什么用,父皇的心目中只有青雀,没有我。他迟早会把我废掉,立青雀当太子。”
“父皇处死称心,完全是为你好。”
“我什么都不要,只要称心。你,你给我滚,滚开些,滚远些!”
承乾正要把太子妃往门外面推,元昌闯进来了。说来也巧,他见了元昌,就像夜行人看见了灯火一样,很快平静下来,跟着元昌走出“幽会”室,走进集贤馆,两个人坐下来,宫女上了茶。承乾屏退左右,元昌喝了两口茶,问道:
“刚才跟太子妃闹什么?”
“我心里闷得慌,跟称心说几句心里话,她出来干涉,惹得我发怒。”
“咳,太子殿下,我说你呀,要是在小事上纠缠不休,抛开大事,那可就完啦。”
“照你的意思,我该怎么办?”
“报仇!”
“原来咱俩都想到一块儿来了,我正想杀了青雀祭奠称心,可惜无从下手。”
“杀死他,可以解除心头之恨,但不能解决根本大计。”
“怎样才能解决根本大计呢?”
“效法玄武门,逼皇上退位。”
“反叛?”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你当上了皇帝,逼宫就变成了禅让。谁敢唱反调,他就犯了欺君之罪,就可以杀他的头。”
承乾咬着嘴唇思忖了片刻:“篡夺皇位,可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必须做好周密的安排。”
“对,赶快把众人召集拢来,合计合计,拿出一个行之有效的方略。”
当天夜晚,同谋者都集中到了东宫西侧崇文殿的密室内,秘密策划叛逆事宜。坐在主位上的承乾两只眼睛红红的,又有点发直,俨若一个被人追捕的逃犯,紧张得浑身的血管都像是要炸开了一般,左看一眼,右看一眼。而后他把目光收回来,望着自己的胸前,嘶哑着嗓子低声说道:
“父皇听信谗言,不把我当太子看待,我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只有豁出去,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求取生存。”
“豁出去,豁出去!”众人七嘴八舌地喊喊叫叫。
侯君集不愧为军事家、谋略家,他倒是沉着稳重,镇定自若地坐在一侧想心事:“太子愚顽恶劣,成不了气候。不过,首先还得利用他,事成以后,再对他下手,那样比反手还容易。”他力主篡位,伸出手来对承乾说:
“臣的一双好手,呈献给殿下使用。”
“有爱卿调度军马,大事成矣。”承乾的脸上显现出欣喜的颜色。
“部署军马得悄悄进行,当前要靠李将军刺探今上的一举一动,才好有针对性的采取行动。”
李安俨站起身来表示说:“我早已将身家性命托付给了太子,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听凭差遣。”
“我们和李将军长的是一个心眼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赵节、杜荷和贺兰楚石等人异口同声说。
参与密谋的人都板着面孔,态度凛然,寒气逼人,室内充满了一种紧锣密鼓、磨刀霍霍的紧张气氛。李元昌觉得不宜把弦绷得太紧,需要松弛一下,他做了个滑稽动作,用风趣幽默的腔调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本王只有一个要求,事成以后,殿下把今上身旁那个弹琵琶的念奴赏给我,就心满意足了。”
“一个美女太少了。”赵节忽闪着金鱼眼,“王爷年轻力壮,至少得赏赐一群,组成一个乐班,才够享用。”
“赐给驸马爷还差不多,我可受不住。”
“呵呵呵呵,”赵节佻薄地淫笑着,“王爷的本领众所周知,没日没夜地荡漾在春水里,也不会被淹死。”
“喂,喂,诸位,”侯君集双手拍了拍,“天快亮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魏王得到今上的宠爱,眼下要谨防太子遭受隋朝太子杨勇那样被废为平民的灾祸。太子殿下,今上召见你时,可要加强戒备呐。”
元昌看出火候到了,适时地提议道:“凡同谋者都要割破手指尖,用帛擦血,烧成灰烬,和在酒里饮下,发誓同生死共患难,准备率军进入皇宫。”
众人饮干血酒,赌咒发愿后,杜荷更加壮了胆。他凑到承乾跟前说:“天象发生了变化,得赶快行动以应天象。殿下只需称得了急病,生命垂危,今上必然会亲自前来探视,乘此机会可以得手。”
天亮后,密探向承乾禀报了齐王李祐在齐州叛乱的消息。承乾又庆幸又洋洋自得,对纥干承基等人说:“东宫的西墙与大内的东墙就是一垛墙,东宫跟大内相距不过几十步,和卿等谋划大事,可谓举手之劳。我们的优势齐王怎么能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