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大帝(下)
作者丨杨友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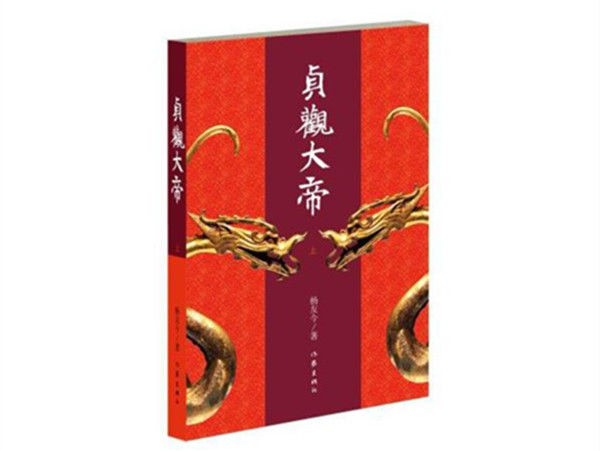
第四章 叛逆
得到白雪公主的死讯,李世民从并州急急匆匆地赶回了长安。可是他回迟了,公主已经下葬。李世民上坟祭奠以后,回到承乾殿,仍有无限哀怨横亘在胸中,无法排遣。他痛苦地歪着头,嘴角旁的两道褶纹颤动着,心头一阵刀剜般疼痛,一阵灼热,眼睛被一层迷茫的水雾给蒙住了。长孙敏端着一碗燕窝粥走到他跟前,温言软语地说:
“二郎,你一直没有进膳,喝点儿粥呗。”
“我不饿。”李世民推开递过来的碗,“只想单独呆会儿。”
“人死不能复生。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好啦。”
“旧情难忘哇。”李世民心中泛起一股酸楚的感觉,“况且,我总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她是自作自受,王府上下并没有人欺负她,甚至可以说对她既尊重,又宽容。”
“我至今还没有弄清楚,她为什么要跑,要死?”
“我弄清楚了。”随着传来的声音,长孙无忌跨进了门槛,“里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太子帮想利用她来激怒你,逗得你先动手,他们好在自卫还击的名义下把你打下去。”
“果然?”李世民惊得目瞪口呆。
“也许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如今太子正在招募骁勇武士,组建长林军;还让右虞候率可达志从李艺那里征调了三百名精锐骑卒,配置在东宫东面的各坊,充实东宫的常备卫士。”
“老兄,你来得好,如果不及时提醒,我真会去跟他拼命。”
“我正是怕你想横了胡来,因此迫不及待地赶来了。”
“如何应付?”
长孙无忌扬起下巴思考了片刻:“赶紧取得证据,奏明皇上。”
“说干就干,我马上去东宫走一趟。”
“你不宜出面,”长孙敏制止道,“要设法让他人看见东宫的新卫士,使太子无法抵赖。”
“好法子。”长孙无忌表示赞同,“二郎你发送几份请柬,邀请萧瑀、陈叔达、封德彝和宇文士及等大臣到秦王府赴宴。等他们路过东宫时,只要稍许留心一下,就会觉察出里面的动静。”
“事情就交给你和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去办理好啦。褚遂良虽说年轻,但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已经超过了他父亲褚亮,而且处事谨慎,对我很忠心。”
萧瑀等人接到请柬,午后便动身去秦王府。路过东宫时,忽然听到宫内传出来一阵阵喊杀声,以及兵器的撞击声。陈叔达怔了一下,指着东宫问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圆滑的封德彝怕惹是生非,缓缓往马轿侧面退,避开陈叔达的视线。宇文士及仔细听了听,说:“好像是操练人马。”
这时候,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和褚遂良迎了上来,拱手施礼道:“秦王命我等前来迎候。相爷们怎么停顿下来了?”
“里面是不是在操练人马?”宇文士及想验证一下自己的判断。
“启禀相爷,”长孙无忌回答说,“东宫最近建立了一支长林军,天天都在进行实战演习。”
“当真?”
“相爷们请随我来。”
长孙无忌带着宇文士及等登上一座高楼,俯瞰东宫,只见宫内广场上分左右排列着数百名将士,轮番用真刀真枪进行操练。将台上站着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和魏徵、王珪、韦挺、冯立等人。李元吉显得特别活跃,跳来跳去,不时凑到李建成跟前,仿佛在向他介绍情况。萧瑀等人觉得事关重大,不敢隐瞒,只得放弃赴宴,随即乘车进宫,奏明皇上。
东窗事发。李建成和李元吉惊慌失措,硬着头皮走进两仪殿,跪倒在丹阶下。李渊眼睛瞪得滚圆,愤怒的光芒如利剑般地射将出来:“谁指使你们搞的长林军,给我说清楚。”
“是儿臣自己想出来的,”李建成低下头对答说,“没有人指使。我是想组建一支卫军,分别驻守左、右长林门,加强东宫的防卫。”
“左右十二卫统领禁卫军,由二郎担任大将军。你却背着朕纠集武力,建立长林军。用意到底何在?”
“父皇明鉴,儿臣仅仅用于防卫,并无他意。”
“马上给我解散。”
“儿臣遵旨。”
“还有,你向燕王李艺征调三百名精骑干吗?”
“打算补充东宫的常备卫士。”
“废话!”李渊一拍御案,“朕不降旨,谁敢征调军马,就要谁的脑袋。立刻把骑士退回去!”
“遵命。”
事后,李渊把率可达志贬到了嶲州。李建成好汉做事好汉当,没有推卸责任,更没有把策划者李元吉说出来,兄弟俩的关系又更加深了一层,更加密切了。一计不成,李元吉又心生一计。他皱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毛,凶相毕露地说:
“愈防愈被动,不如转守为攻,干脆一刀捅死他。”
“不行。”李建成摇了摇手,“兄弟犹如手足,打死还是亲兄弟,搬兵要搬父子兵。二郎所采取的也是防范措施,并没有迹象表明要杀我们。”
“等到他动手,我们可就来不及喽,防也防不住喽。”
“事实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到那个时候再说,好不好?”
“大哥,二郎不死,你我休想睡安稳觉。”
“你再让我好好想一想。”李建成有些拿不定主意。
李渊一心想化解三个儿子之间的矛盾,带着世民去元吉的住处走动。建成先到一步,元吉双手握成拳头尖毒地说:
“机会终于来了,今晚你就看我的。”
“你要干吗?”李建成抬了抬眉毛。
李元吉伸出一只手往下一劈:“宰了他。”
“别干傻事。惊吓了父皇,那可罪不容诛咯。”
“只要于大哥有利,我三胡出生入死,也在所不惜。”
李元吉命护军宇文宝等人埋伏在暗室里面,以掷盏为号,刺杀李世民。掌灯时分,李世民跟随李渊来到了武德殿后院,李建成和李元吉恭迎至正殿,摆酒设宴,李世民发现气氛不正常,眼睛紧紧盯住了元吉,注意他的一举一动。李渊显得颇轻松,笑吟吟地举起酒杯,对三个儿子说:
“我当了皇帝,天下惟我独尊,可以说心满意足了。人生别无他求,只希望你们莫忘手足之情,尽弃前嫌,言归于好。一家之计在于和,只要你们兄弟友爱,就是尽忠尽孝,来,一起干了手中的酒,愿你们从此和睦相处。”
父子四人干了杯中的酒。元吉又敬了两巡,然后把目光转到李建成的身上:
“大哥,先头你说内急,干吗还憋着?”
“噢,噢,父皇恕罪,儿臣离开片刻即来。”
李建成转身离席。李元吉给李渊斟满了酒,说:“请父皇满饮一杯,儿臣一定尽忠尽孝,跟大哥同心同德。”
“三胡,”李渊沉下脸来厉声说,“你不要耍滑头,话里藏话。朕明明教你们三兄弟和衷共济,而你偏偏违抗父命,厚此薄彼。该当何罪?!”
“别人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巴结不上,怪不得我。他不仁,我不义,儿臣是被逼不过,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
元吉拿起酒杯,准备砸下去。李建成迅疾返回殿堂,抓住元吉的手,把杯子夺了过来。李渊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李建成已把杯中的酒倒进了嘴里:
“让我代四弟饮干杯中的酒,以示不忘父皇的教诲。”
李世民见元吉和建成都坐下了,推测危险已经过去,才跟着吃喝起来。
谋杀二郎未果,三胡气得扭歪了嘴,愤怒地责备大哥道:“我是替你着想,其实杀不杀他对我并无多少关系。”
“你恨他,我更恨他,兴许超过你十倍、百倍。可是,这样行刺,一则过于鲁莽;二则惊动圣驾;三则嘛,对于白雪公主的死,他没有告御状,也没有找我的麻烦,我欠了他的一份人情。今后随你怎么干,我再不干涉了。”
“我说你是个呆子,看来你比呆子还要呆,还要傻。常言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要想办成一件大事,不心狠手辣,下不得手,能成功吗?从今往后,我也不再过问你的事了,你好自为之吧。”
“三胡,”李建成亲切地喊道,“对也好,错也好,权且放过他一次,下不为例。日子长着嘞,机会多的是,别泄气,咱兄弟俩从头来,到时候你再看我的。”
炎夏酷暑,燠热难耐,李渊前往渭北仁智宫避暑,命李建成留守京师,李世民与李元吉伴驾随行。李建成嘱咐李元吉抓住机会谋害李世民:“是安是危,就看今年。”李世民伴随父皇来到仁智宫,无心观赏歌舞,也很少游玩,多数时光都在阅读兵书,思考战策,老君赐给他的三卷天书差不多都快翻烂了。长孙敏端茶进门,见他又在伏案读书。她打趣地说:
“几卷天书,没有看上一百遍,至少也有几十遍了。”
“古人说,温故而知新。天书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收获。”
“近几年,你的学问进步很快哩。”
“书山有路勤为径,”李世民不胜感慨。
“学海无涯苦作舟。”长孙敏把下联对了起来。
“学问倒谈不上苦不苦。”李世民神情忧郁,“我内心的痛苦,可能只有你清楚。”
“还是父皇说得好,一生之计在于勤,一家之计在于和。”
“提到‘和’字,我就感到惭愧。咳,”李世民的额头皱起了抬头纹,“我们兄弟三个,始终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辈子只怕很难和好了。”
长孙敏眼珠子转了转:“先头潇湘公主来找她姐姐,你见到她没有?”
“没有。”李世民心头激灵了一下,“她明知她姐姐没有来,该不会有其他事吧?”
“怪哉!问过你我的起居饮食,她便转回去了。”
“很可能隐含着一种暗示,不妨处处留心一下。”
李世民挑灯夜读疲倦了,伏几而卧,忽然窗外伸出一个头来,向内窥视着。雷云吉和雷云兆追到外面,黑影一闪,不见了;侧耳细听,只听见蟋蟀在草丛中或石壁下口瞿 口瞿 口瞿 地嘶鸣着,此唱彼和,仿佛在演唱快节奏的曲子。
留守京师的李建成得知李渊已在行宫安居下来,立刻召见尔朱焕和桥公山,吩咐说:“庆州都督杨文干招募了数千壮士,正在加紧训练,你们运送一批铠甲去,催促他赶快起事,我与齐王跟他内外呼应。”
“杨都督在东宫做侍卫时,我们跟他打过交道。”尔朱焕提出了质疑,“他为人机灵有余而缺少气度,左右逢源却不得人心,看来只可利用而不可重用。太子过份器重他,怕不怕翻船?”
“你们照我的安排去做就行了,不必考虑那么多。”
二将领命而去,押着运送甲胄的车辆向北渡过了渭河。走到彬州三岔路口,尔朱焕约束车马停了下来,就近投宿。
“天色不早了,今日歇下,明天赶路吧。”
“鬼天气,”桥公山兜脸抹了一把汗,“热得不透风,快把人给闷死啦。”
其实当天走的路不多,人马并不累,只不过二位将军紧张得全身松软,都想停下来冷静地揣度揣度,作出最后的选择。叛逆对于他们来说并无多大的好处,并且名不正,言不顺,成功也没有几分把握。两个人喝了一阵闷酒,觉得不是滋味,想寻点事消遣。要消遣,除了嫖,就只有赌。心境不佳,去青楼没有兴趣;赌,两个人只能掷骰子。桥公山耐不住寂寞,提议说:
“光喝酒,愈喝愈躁,不如掷掷骰子,排除一下心中的烦恼。”
“赌,本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尔朱焕借题大发议论,“人的一生,始终离不开赌,跟自己赌,跟别人赌,赌输赢,赌命运,赌升官发财。”
“还有赌运气,尔朱兄,你说是不是?”
“运气嘛,我也说不准。比如说,太子要和皇上过不去,依你看,谁的运气好?”
“你问我,还不如问骰子。”桥公山掏出两粒骰子捏在手上,“掷出的骰子点数相加,单数,皇上会赢,双数就是太子赢。”
“老弟,问骰子,还不如问自己的心。”
“我如今心上心下,没有定准。”
“哎呀,不如实话实说,你是怀疑太子仓促举事,成功的希望渺茫。”
“你呢?”
“无疑也是我的看法。”
“噢,原来咱们想到一块儿来了。你怎么不早说?”
“现今说出来,正是时候。”尔朱焕呷了一口酒,“从三岔路口朝北走,是庆州。投东走,便是仁智宫。”
“去仁智宫干吗?”
“觐见皇上,自首投案。”
“看来你我又想到一块儿来了。”
“只要不是傻瓜蛋,谁都会想转来。”
尔朱焕和桥公山一起策马驰往仁智宫,告发了太子命杨都督起兵反叛。李渊吃惊得只觉天旋地转,又气又急,他反复想了想,以亲笔诏书传李建成前来仁智宫见驾。
李建成接到诏书,心一下子紧缩起来,毛发倒竖,汗像洗澡一样涌流。他举棋不定,左右为难,不知是去好呢,还是不去为好?然而正值危急时刻,太子中允王珪和洗马魏徵都不在身边,他急得如同失了魂一样,心脏狂跳,茫然乱转。徐师谟意识到太子总是瞥着他,心里直发毛,想说又不敢冒失开口,只好往后靠了靠,退避到一旁。殿堂充满一片紧张不安的气氛,似乎东宫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开口说话呀!”李建成双手一张一扬,“平时个个能言善辩,馊主意一套又一套。今天怎么都成了哑巴?”
“身为太子宫的人,自然要替太子着想。不过,”徐师谟低着头申明道,“万一讲错了,怕吃罪不起。”
“有话尽管大胆说出来,我不会计较。”
“殿下若去行宫,”徐师谟抬起头来,“属下以为凶多吉少。事已至此,别无选择,惟有铤而走险,据城起兵,先杀秦王,然后逼皇上退位。”
“留守京师的兵力有限,围得住仁智宫吗?”
“可以边围边调集兵马。”
“调不调得动?”
“打着救驾的旗号,天下都会响应。”
“那么,逆贼指谁呢?”
“当然是李世民。”
“朝廷内外掌管兵权的将帅,多数是他的旧部呐。”
对话中断了,静默又占据了整个殿堂。踱动中的李建成转得两腿像灌了铅一样,愈来愈沉重,迈不开步子了。他的心也像腿一般沉重,交错着许多复杂的情结:反叛又怕不得人心,请罪又怕父皇治罪,左难右难,下不了决心。赵弘智看到太子窘迫到了慌乱的程度,捻着吊在下巴上的一小撮胡子,边用心思边进言道:
“仓促举事,控制京师,或者围攻行宫,显然是往刺丛里钻,此路不通:一则,满朝文武,三军将士,多数不会服从太子的号令;二则,皇上既已察觉,身旁又有秦王……”
“不要提他,”李建成打断了赵弘智的话,“我恨死了那个祸种。”
“提他也好,不提也罢,总之,皇上肯定进行了部署。在被动的情况下,最好的法子,莫过于负荆请罪。”
“我去见父皇,岂不等于送肉上砧板。”
“非也。”赵弘智立定在原地,“常言道,虎毒不食子。皇上宽厚仁慈,殿下乃皇上的嫡长子,见了面,心自然会软下来。”
李建成记起了魏徵的警告:“矛头只能对准秦王,而不能指向皇上。”他长嘘一口气,仿佛把涌到喉咙眼儿的心又回复到胸膛里去了,决计免去太子的车驾仪仗,屏除随从禁卫,觐见父皇乞请恕罪。北行到距仁智宫六十里处,李建成把所有属官都留在毛鸿宾堡,身边只带十几名侍卫骑马相随。来到行宫,跪倒在李渊跟前,伏地磕头请罪。李渊扭歪了脖子,灰白胡子一颤一颤地,眼珠子像火球一样直射着李建成:
“瞧你干的好事,快把朕气死啦。”
“父皇恕罪,儿臣一时鬼蒙了头,如今才清醒过来。”
李建成的头磕得地面咚咚响,用力过猛,磕破了额头,血流满面,几乎晕死过去。裴寂见状,跪下来求情说:
“皇上,太子已经不成人样了,饶了他吧。”
“活该!”李渊怒气未消,猛一顿足,“押下去,听候处置!”
当夜,李建成被软禁在禁卫军营里,只给他麦饭充饥,由殿中监陈福看守。李渊派遣司农卿宇文颖急往庆州召唤杨文干,元吉暗地勾结宇文颖,叫他把真实情况告诉杨文干。杨文干得知事情败露,举兵反叛,李渊命令左武卫将军钱九陇,会合灵州都督杨师道,兴师镇压,杨干文攻陷了宁州,李渊召见李世民商量对策。李世民嗤嗤鼻子,从内心深处倾泻出极大的轻蔑和仇视:
“杨文干不过一名小丑,干出狂悖的勾当,想必他的僚属很快会醒悟过来,将他擒杀,即令不会,也只须随便用一员将军前去讨伐,就足够了。”
“不行。”李渊对事态看得颇严峻,“杨文干的事关连着大郎,恐怕会有许多人响应,你最好亲自走一趟,回来后,便立你当太子。朕不愿意效法隋文帝杀害亲生儿子,届时改封大郎当蜀王,蜀中兵力薄弱,以后他如果能够事奉你,应该保全他的性命;倘若不服,制裁他也易于反掌。”
仁智宫建造在万山丛中。李渊担心叛军突然袭击,不敢安枕,连夜率宫廷禁卫从南面开路下山。走了数十里,跟东宫的官员卫士相遇,李渊强令他们三十人为一拨,分派禁军从中隔开,并紧紧围住。
更深夜静,大地沉睡着,万籁俱寂,而仁智宫却并不安宁,磨刀霍霍,杀机四伏,李世民彻夜未眠,一直在寝殿内踱步。长孙敏把一件单衫披到他身上,关切地说:
“山间清凉,夜晚风大,要注意冷暖。”
“我一直感到燥热,”李世民咳了咳,“背脊还在出汗。”
“心静自然凉。你心神不宁,所以觉得热。”
“太子关了禁闭,我内心倒是平静了。敏儿,你预测事态会朝哪方面发展?”
“太子不死,终究为患。”
长孙敏的话还没有落音,潇湘公主趔趔趄趄走了进来,急急巴巴地说:
“王兄,王嫂,有紧急情况。裴老儿告诉三胡,皇上打算改立王兄当太子,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要联合尹德妃和张婕妤,以及朝廷的大臣,替太子说情。”
“父皇立我做太子的话,我早听腻了,从来没有把它当过真。”
“要是大哥死了,太子位置不就轮到了你么?”
“弟妹,父皇不会处死太子。”
“你与太子,是天生的冤家,有他无你,有你无他。”
长孙敏点了点头:“公主的话,可谓一针见血。”
“我的来意,就是奉劝王兄乘乱动手,除掉太子,以绝后患。齐王和太子共裤连裆,太子不死,根本无法拆开他们,他跟太子必然落入同样的下场。保护王兄,事实上也连带保护了齐王,同时也保护了我们姐妹俩的安全。”
“行刺,暗算,”李世民眉头耸立起来,“都是小人行为,我做不出来。”
“失去今晚的机会,往后可就困难呶。”
“谢谢你的好意,快回去歇息。”
天一亮,李世民打点行装下了山,李渊接着返回了仁智宫。李元吉和裴寂非常活跃,内外沟通,替李建成说好话,说服李渊打消改立太子的念头。太子妃柴氏一路颠簸,从长安赶到了仁智宫。她哭哭啼啼,跪到李渊的膝下,哀求宽恕太子。
“父皇,太子一时心血来潮,铸成大错,可他的矛头所指,决非父皇,而是二郎。二郎用心险恶,阴谋夺取太子之位,太子几乎被他逼疯了。”
“不管是疯是狂,”李渊语调生硬,“犯了叛逆罪不可饶恕。”
柴氏的嘴被堵住了。尹德妃眼珠子转了转,岔开了话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儿子错了,老子可以教训他,但还是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李渊沉吟未决,欲言又止。张婕妤一壁厢跟李渊捶背,一壁厢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子不教,父之过。以臣妾看来,皇上也有家教不严的过错。”
“父母难保百年春,他人大心大,我保不了他一辈子。”
“妹妹的‘家教’二字,皇上别理会错了。”尹德妃辩解说,“把话说穿,凡属皇上的儿子,手掌手背都是肉,既要管教,又要一碗水端平。二郎那么猖獗,处处威胁太子,太子是在危急的情势下干的蠢事。”
“错了就改,也是好事。”张婕妤又把话接过来,“而今太子已深切悔悟,应该宽大他。”
“皇上别气了,气过了头,有伤龙体。”
尹德妃和张婕妤一搭一档,像二重唱似的,唱开了李渊的心。柴氏退下去后,李元吉和裴寂又轮流着来替李建成辩护、解释。他们又用厚礼贿赂中书令封德彝以中间人的姿态出来说话,封德彝潜持两端,阴附太子,他的固谏和剖析,可以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彻底解除了李渊夺宗换嗣的打算。当蓬头垢面的李建成出现在李渊面前时,李渊瞧见他那憔悴的形样,顿生怜惜之情,赐了他的座位,和颜悦色而又语重心长地告诫道:
“谋叛事件的确有可原谅的地方,在于你不是想篡位,而是怕二郎夺嫡。告诉你,要保住太子的地位,关健在于你自己。你干得好,众人拥护,朕何必更换太子,况且你是嫡长子。”
“父皇圣明,”李建成离座跪拜道,“儿臣心悦诚服。”
“起来吧,朕还有话说。兄弟中你居长,要起表率作用,既要讲究友爱,又要善于容忍、迁就,不必斤斤计较,更不可反目成仇。”
“儿臣谨记父皇的教诲。”
“你明白了朕的一片苦心就好,但是切切不可口是心非。”
李渊仍命李建成回长安居守,而把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东宫属员王珪、韦挺,以及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把他们流放到了嶲州。杜淹与杜如晦叔侄之间内心不和,在天策府不受重视。他心生怨叛,倒向了东宫,时常通风报信,或者给李建成出谋划策。
李世民率领兵马进抵宁州,对叛军展开了攻势。杨文干军心动摇,在败退中不断溃散,最后被部属刺死。唐军擒获叛将宇文颖,斩首。李渊得到平定叛乱的奏报,返回了长安。李世民马到成功,旗开得胜,班师凯旋。李渊命太子李建成率百官迎于郊外,摆设庆功宴,犒赏三军将士。
庆典隆重而热烈,李渊亲自举杯祝酒,他脸上笑眯眯的,而对于立世民当太子的事,却似乎乐得忘记了,不再提及。李世民心中很不是滋味,然而有口难言。秦王府的属官都愤愤不平,闹闹嚷嚷。尉迟敬德紫黑的大脸盘也扭歪了,心头腾起一把无明火,按捺不住倾吐出来:
“天子金口银牙,说话也不算数,耍起无赖来了。”
“休得无理。”李世民瞪了他一眼,“父皇自有他的谋算。”
“哄人好比软刀子杀人,”秦叔宝也气黄了脸,“王爷你可得当心点儿。”
侯君集跳出来,又点了一把火:“皇上明显在袒护太子,连谋反也不治罪。王爷打的胜仗愈多,功劳愈大,他的猜疑也愈大,压得愈厉害。”
“与其受鸟窝囊气,”程咬金倒竖起毛楂楂的红胡子,“还不如反了。”
“你敢!”李世民站了起来。
“杀了太子,不就万事大吉了么?”
“元吉那小子更坏。”侯君集在火上又浇了一瓢油。
“连他也砍了。”程咬金接应道。
李世民睁圆了眼睛;“你们今天怎么哪,是不是要把我推到炭火上去烤?”
“常言道,不平则鸣。”房玄龄捋着山羊胡子,倒是显得颇沉静,“自晋阳起兵以来,皇上三番五次要立王爷当太子,但是一再食言。太子与齐王合伙谋害你,一次比一次升级,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王爷老忍让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你让步,他反倒以为你怕他。要是回击一下,说不定还能打下他几分狂妄劲。”长孙无忌进一步作了一番鼓动。
杜如晦觉得分量还不够,扭动一下肥胖的身躯,慷慨激昂地说:“长痛不如短痛,不下手则已,一下手就要干他个干净彻底。”
议事堂的情绪愈来愈激动,众人叫叫嚷嚷都不服气,要起来闹事,而且打算闹翻,翻它个底朝天。李世民也受了感染,血液一股一股地往上涌,全身起了一种潮热。他踱了几步,平静了一下心态,然后低声慢语地说:
“诸位的肺腑之言,我都听进了耳。目前的情形,谁都明白,我和太子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没有调和的余地了;不过,如果没有充分的事实作依据,理由不充分,贸然行事,难以封住天下人的口,将留下千古骂名。因此,必须做到有理有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方可行动。史家的传统从来都是秉笔直书。司马迁受了腐刑,仍然直言不讳,坚持把《史记》写完。春秋时期,齐国的崔杼弑杀了国君,太史立刻把他的罪行记在史册上。崔杼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照样那么写,先后又被处死。太史的小弟还是那样写,崔杼别无他法,只得让他如实记录下来。”
“大王前怕狼后怕虎,”尉迟敬德顶了一句,“再拖下去,只怕会要拖到他们来取你的首级。”
“不到时候,我决不动手。”
谈话中断了,各人的内心活动却异常复杂,翻肠倒肚,活像火山爆发前岩浆的躁动。
丘行恭擤了擤鼻子:“我倒有个好主意,不妨在东宫和齐王府暗设底线,等到摸准了情况,掌握了事实,便进行反击,那样就有了理由。”
“好一个强盗,”程咬金眉梢挑起一丝友善的嘲笑,“恶性不改,亏你想得出来。”
“假使我是强盗,那你便是土匪。”丘行恭反唇相讥道,“咱俩半斤八两,和尚碰了秃子。比较而言,我还只能算一个小毛贼,而你当年却是瓦岗寨的大强盗,混世魔王。”
堂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长孙王妃和南康公主磕磕绊绊走了进来。公主抱住李世民,哽哽咽咽哭诉道:
“二郎,三胡把潇湘妹妹关起来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李世民让南康公主坐下来,“别哭啦,慢慢说。”
“缘由你我都清楚,”长孙敏摇了摇手,“不用说啦。”
“是不是在仁智宫时,潇湘公主劝我趁乱除掉太子,他们查出来了?”
“正是。”
“二郎,快去救妹妹哇!”南康公主急得喊起来。
“公主不会有性命之忧。我去的话,反而会促使三胡下毒手。”
“他还打了她。”
“三胡是个火爆性子,来得快,去得也快。等他的火气消了,再设法营救潇湘公主不迟。”
“你不去,我去。”
南康公主赌气推开李世民。李世民又把她扶到座位上:“谁去都一样,对潇湘公主有害无益。”
“那可怎么办?”
“让它冷把火。等到父皇召见我时,我请父皇出面说话,吩咐三胡把潇湘公主放出来。”
长孙敏替南康公主揩干眼泪,拉着她站了起来。李世民转身一瞧——嗬!——堂内的人全都走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