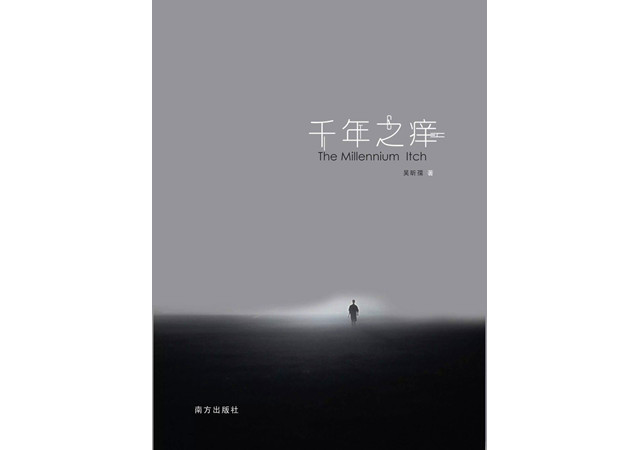
千年之痒
作者丨吴昕孺
第二章 虚空中最为虚空的那部分
乌去纱每个月回罗岭家里一次。罗岭是高桥镇下辖的一个村,高桥茶厂正在他回家的路上。好大一个厂子,厂牌挂在马路边一堵红色砖墙上,这堵砖墙在田畴间尽可能绕了一个大圈子(圈子里面矗立着高大的厂房和整齐的宿舍楼),然后从远处很不情愿地回来。因为闹着情绪,回来了还不愿意合龙。隔着约十来米宽,没有合龙的这一段就用两张铁门拢起来。“高桥茶厂”的牌子挂在铁门西边。
铁门前面是橘洲至平江的省级公路,简称橘平公路。对面是大片大片连绵不绝的茶山。晴天望过去,好像在地上铺了一块绿色锦缎。雨天望过去,宛若波翻浪涌的海洋,一直接到天际。阴天望过去,恰似云遮雾绕的仙境,一痴愣,说不定能看见一位仙子飘然下凡。乌去纱回家或从家里返校,经过高桥茶厂时,都会慢下步子,在各种天气里欣赏茶山的气质变化。他曾经想过爬到茶山上去看看,爬到最高的山顶上,看看那边什么样子,是不是还是茶山,或者是一片藏有野鸡和松鼠的杉树林呢?但每次因为急于回家、返校,只能把这个愿望放在心里,放飞一下想象的翅膀,脚步则依然沿着蛇一样曲折的公路前行。
初春时节,南方的雨来了精神,雨丝虽细,却密不透风,织成一张严严实实的网。星期六,乌去纱背着书包,挂上雨披,得回家拿生活费了。出校门走四百多米上橘平公路,右拐爬上一个高坡,下坡以后连续五个“之”字形大转弯,再走四五里平地,接着一个270度的转弯加超过30度的上坡,弯转完了,坡还没有上完。转完弯就能看到高桥茶厂的厂房、宿舍楼、自来水塔和烟囱,它们像是一个早就等在那里的团体,等着你的加入。看到你来了,它们露出高兴、迎人的笑容。当你走近,继续保持着它们难以企及的角度,眼看便渐行渐远。它们在你距离最近而又明确不能拉你入伙时,一齐睁大眼睛瞪着你,恨不得伸出胳膊把你扯进门里去。平时没留意,这次他被这突如其来的阵势吸引住了。站在高桥茶厂大门前,呆呆地望着关闭的铁门上开着的一扇小门。那扇小门大方地表示着友好,仿佛在说,你不入伙,请等会,要送样礼物给你。他就等了会,三分钟后,乌去纱正要走人,那扇小门“咣啷”一声,钻出一只自行车轱辘。车轱辘昂着头跨出小门,也带出了它后面的同伴和扶着车身的主人:一位穿着红色塑料雨披的女生。
啊,是她!
乌去纱一惊。他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候近距离看到吴盈盈。她也望见了乌去纱,目光似比在教学楼上柔和妩媚,没那么冷艳。太近又太突然,乌去纱怕过于唐突,没有多看。他这一撤,吴盈盈就骑到了车上,没入雨中。待乌去纱回过神,都不知道那辆自行车往哪个方向去了。这样的雨天,外面没有一个人,她为什么会出来呢?她去了哪里?她也许是专门来见我的,冥冥中,我们要在这里碰上一面。乌去纱在欣慰中感到沮丧,倘若自己一直看着她,她或许就不会那么快骑到车上去,不会在眨眼间消失,只留下这张空荡荡的雨网。
第二天,乌去纱早早吃过午饭,准备返校。妈妈说:“平时回来要催你上路,生怕你赶不上学校的晚饭,今日怎这么急,吃完饭总得喝口水!”乌去纱脸红了,只好把背上的包放下来,端着妈妈刚泡好的茶。哎呀,好烫,等到喝完这碗茶,至少得十多分钟。乌去纱等不及,嘬起嘴唇在碗边上来回溜几圈打湿嘴皮子了事。
离开家,经过三里疙疙瘩瘩的简易马路,上橘平公路。特别是下雨之后,简易马路成了泥浆王国,有些地方连放只脚的空当都没有。要不得使劲跳过去,这样的危险性在于如果对距离估计有误,或者用力不够,那么脚落下来的时候可能仍处于泥浆地带,后果将是一塌糊涂;要不索性踩在稍浅的泥水里,放任鞋帮、裤腿与泥水的缠绵。终于上了柏油路,乌去纱在路边狠狠顿了几脚,算是终结了泥浆侵略扩张的美梦,让自己的脚步变得轻快起来。
一上柏油路,便要转一个很大的弯。弯角上窝着一栋红砖平房,虽小,却显出与乡里村舍迥然不同的神态。它的门漆成绿色,上的是嵌入式、可以从后面反锁的防盗锁。窗户蒙着绿色窗帘,远看若有若无,近看像挂起来的筛子。这栋房子人们叫它水文站。它看守着公路与群山之间的一条河流,仿佛一只蹲坐在地上、伸出舌头、警觉地望着远方的猎犬。过了水文站,走五六里平路,两边是长着秧苗的田野。再爬上一个长坡,大客车爬这个坡都会吭哧吭哧直喘气,爬到顶上便能看到高桥镇的全貌。但要到镇上,下了坡后还得走三四里,再爬上一个陡坡。这个坡陡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坐在客车里,总觉得客车在向后退,而不是向前跑;如果你和汽车一起上坡,你会担心汽车上不去,从而退下来压着你;如果你上坡时碰巧没有汽车,那就好比在攀爬一堵绝壁,镇上的第一栋房子——一个小五金店伫立于绝壁之巅,仿佛上面伸出的一只拉你的手。
高桥镇由散落在橘平公路两侧的数十栋民居和两三栋楼房组成,延伸约二百米远。由小镇再往东走两三里,到高桥茶厂。茶山则是从镇上就望得到的。乌去纱一到镇上便放慢脚步,他东张西望,像一名悠闲的游客而不是一个赶路的学生。不过,即便这样,他也很快到了茶厂门口。大门右下边(他望过去是左边)的小铁门和昨天开得一模一样。他站在离门约十米远的地方,像平时在玉兰树下望向二楼一样望着它。三分钟后,小门里蹦出两个小朋友,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带着比她小三四岁的男孩。男孩手里拿着一个铁环,却没有在地上滚。他们没有看他一眼,径直往镇上的方向跑去。又过了三分钟,小门“咣啷”一声,钻出一只自行车轱辘。车轱辘高昂着头跨出小门。乌去纱心里猛地一紧,全身血液像接到命令似的,一齐涌向脑门,旋即狠狠地跌落下来,四散逃窜,只留下乌去纱一张不好意思的关公脸。骑自行车的是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后面跟着一只浑身湿透的丑陋的小狗。小狗甩着耳朵,好奇地看着乌去纱,它拐过来几步,想和乌去纱套套近乎,被中年男子的吆喝声喊走了,它频频回头看着乌去纱。乌去纱哑然失笑,步子迈得比车轱辘还快,回了学校。
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课间时,楼上那双眼睛仍然望过来。尽管乌去纱无数次告诉自己:她十有八九不是望着我。如果她真是望着我,目光怎会那样平和,平和中还带着冷傲呢?即使她是望着我,也不是心仪和喜欢的那种,而是她的目光必须要抓住某样东西。他在她的眼里,和从天上降落的一只瘸腿飞鸟,和玉兰树上一片被虫啃噬过的叶子,和山坡上那盆许多年来被人遗忘的仙人掌毫无区别。甚至他和虚空也没有两样,他就是虚空的一部分,弄不好还是虚空中最为虚空的那部分。
乌去纱平生第一次陷入心理危机,一双本来应该证明自己存在的眼睛,却在证实着自己的虚无。明明进入了她的视野,却被她视为无物。这对乌去纱的自信是不小的打击。接下来,他非常想弄明白那双眼睛和自己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那个叫吴盈盈的女孩,她真的认识楼下这个名叫乌去纱的男生吗?即使不知道他的名字,她真的对这个学习上无往不胜的男生怀着好感吗?这成了搁在乌去纱心里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与遥远的北京大学比起来,它显得多么急切,多么令人困惑。好像一个看上去很容易解答的方程式,但每次计算出来的答案都让人不敢相信。
进入高三后不久,学校发布了举行演讲比赛的通知。每个班选出一人去学校参加决赛。乌去纱被选为60班的代表。他很关心62班的代表是谁,他从歪脖子班主任手中的名单上看到是“邱雁雁”。他也想到不可能是吴盈盈。不要说让她口若悬河,博她一笑都不是易事。但她的冷傲里有一束明亮的光,有一股淡淡的暖意,她即便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仿佛是从辽阔寂寞的沙漠里伸出的一只手,虽然离你那么遥远,它却总是在向你挥动,向你靠近。
演讲比赛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大礼堂就像一艘再也不能远洋航行、泊在岸边供人观赏的大轮船。乌去纱和他的同学们从来没有好好观赏过它,而是一次次走进它里面,接受校长不断重复的训示。同学们说校长喜欢“炒现饭”,现饭他们也得一口口吃下去,横竖是一顿饭,总比没饭吃要好。这话的后半句是歪脖子班主任说的。
全校学生按年级、分班排着队走进大礼堂,整整齐齐坐在舞台下面。舞台上一块绛色幕布很张扬地覆盖了整个后墙,给人的感觉是幕布后面从不曾有过墙,那是另外一个时空,说不定绕过那块幕布就到了宋代,能见到柳永,最好是能见到李师师。据说李师师那双眼睛勾魂摄魄,吴盈盈能与之一较高下吗?幕布前方的正中竖着一个立式麦克风,学校的高个子电工一会儿扯扯电线,一会儿敲敲音箱,一会儿用手在麦克风头上拍几下,嘴里高声大气地喊着“喂,喂,喂”,好像那个包着红布的麦克风里藏着一个不听话的家伙。
乌去纱从座位上站起一看,黑压压一片人头,吴盈盈也在里面啊。他朝62班坐的方向望去,同样黑压压一片。一双美丽的眼睛,固然抵不过这么多黑压压的人头。他听到一个声音,是歪脖子班主任发出来的,要他到后台去抽签。后台是吊在舞台东头的一间小房子,节日举办文艺汇演时,这里是化妆和换装的地方。
乌去纱一进后台,看到一张出乎意料又似乎在他意料之中的面孔。经常站在吴盈盈旁边的那位女生居然也在里面。那她就是邱雁雁了,乌去纱想。团委书记站在一张课桌后面,其他选手散落于房内各处。有人互相说笑。有人在看手里的稿子,嘴里念念有词。有人望着窗户,因为被布密封了,所以望不到窗外去。只有邱雁雁侧着身子紧贴书记,盯住他那只在不停晃荡一把小纸团的手。乌去纱进去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她对乌去纱像老朋友般笑笑,迅疾收回视线。正在这时,书记将手松开,潇洒地一撒,小纸团争先恐后在他面前的桌上滚动。每位选手小心翼翼地捡起自己看中的那个,乌去纱没急着上去,等其他选手都有了,他才捉起桌子上剩下的最后那个。大家打开各自的小纸团,只听得邱雁雁一声大叫:“啊,我是第一个!”乌去纱也打开了,纸条上写着“11”,他将在倒数第三个出场。
演讲题目是“如何做社会主义‘四有’新人”。邱雁雁发挥得很出色,她落落大方,舞台仿佛是她家堂屋,下面坐那么多人,她全当是家里的三姑六舅表姐堂弟。她的普通话与众不同,像抓获罪犯一样地拼命压住自己的舌头。橘洲话一律不转舌,因此橘洲人说普通话,舌头很不听话,只有将舌头死死压住,宁可错转十个,也不少转一个。邱雁雁顺利完成了她的“转舌”伟业,她获得了92分。乌去纱将自己各个方面与邱雁雁进行对比,他觉得无不落处下风。这是一场硬仗!
接下来的果然都不是邱雁雁的对手,除一个打了90分,其他都是80多分。以乌去纱的普通话水准,如果按常理出牌,超过邱雁雁的可能性极小。轮到他了。他拿出一直在学校享有美誉的风度和迷人微笑,走到麦克风前,舌头在嘴里优美地转了一个圈之后,开始演讲: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四有’新人吗?‘四有’新人就是有纪律、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的人。这‘四有’里面,纪律好比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没有纪律就像不穿衣服、光着身子的人,丑;文化好比我们每天吃的饭,不吃饭会饿死,没有文化的人只能做乞丐,迟早会饿死;道德好比我们女生化妆,人的美是三分自然七分打扮,道德就是那七分打扮,有道德的人总是要美一些;而理想呢,好比我们脚上穿的鞋子,不穿鞋子走不多远,我们穿上理想的鞋子,就能一往无前……”
台下掌声雷动。这段话演讲稿上没有,完全是乌去纱同学的即兴发挥。效果出奇的好。他想,如果这次演讲比赛,连吴盈盈身边的“丫环”都比不过,要赢得“小姐”的芳心,是不可能的。乌去纱夺得了96分。在诙谐幽默的语言面前,转舌成为次要的了。上台领奖之前,选手们聚在后台等待,邱雁雁主动到他跟前说:“你真棒!来,握个手,以后多交流。”乌去纱握住她伸过来的手,一时没有放下。这只手与吴盈盈有过亲密接触,它拉扯过她的衣服,梳理过她的头发,抚摸过她的脸……邱雁雁也很兴奋,她尽力张大眼睛,调动起自己眼里所有的光芒,笑得虽然有些傻,却很坦诚。乌去纱抽出手,谦虚地说:“我是乱讲的,你才讲得好,普通话多标准。”邱雁雁听了,夸张地笑弯了腰:
“你要学普通话容易啊!你上山砍过柴吧,说普通话就像上山砍柴一样,不能拦腰砍,要兜底砍,贴着底儿砍。回头你试试,保准一学就会。我可是没有保守,你也要教我几招,不能自个儿掖着。”
邱雁雁说完,腰又弯下去了。乌去纱没来得及回答,就被招呼着上台领奖。一等奖的奖品是:一张奖状,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床毛毯,一块床沿巾。奖品种类体现着获奖等级,二等奖少一支钢笔,三等奖少一床毛毯。乌去纱两只手拿的拿,抱的抱,提的提,左支右绌。同学们看他抱着奖品下台的窘样,颇有节制地起了一阵哄笑。这种哄笑的波长与平日戏谑之笑的波长截然不同,它们表现出来的是佩服与仰慕,是一种不约而同的集体献媚。乌去纱一“讲”成名。他的四寸标准照贴在教学楼中间、楼道两边的宣传栏内,引得众人围观。可惜该死的闪光灯使得眼镜片反光厉害,特别是左眼的镜片,仿佛被一粒子弹命中,几乎击毙了照片上他迷人的微笑。
演讲比赛当天下午,乌去纱恢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每天的正常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诡异,比如现在,他在班上受到隆重拥戴。难以理解的是,这种拥戴开始悄悄拉远他和同学之间的距离,以前还可以呼朋引伴,可以切之磋之,可以讨论争辩,随着他在演讲比赛上的加冕,这些都兀自消失了。同学们认定他一枝独秀,认定了对他的可望而不可即,连每天跟他泡麦乳精和总是等在宿舍拿他脏衣服的女生,也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努力。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谈论他,单个儿想念他,暗地里喜欢他,但只要他在场,或者他一露面,谈论会立即终止,想念会立即不动声色,喜欢更是会盖上漠视的表情。瘦如竹竿的地理老师逢人就说,乌去纱这样的天才哪里去找,一百年才出一个!每次单元考试,他要乌去纱考完后直接把卷子贴到教室墙上,作为标准答案,他就有更多时间给远在五公里之外的女朋友写信了。
这种局面增添了乌去纱的自信,也加深了他的孤独。幸好身边还有唐宏伟和柳志平两员哼哈二将,这两位除了“哼”和“哈”之外,不可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但能够填补他的空虚。越是忙碌越容易空虚。忙碌与空虚这对孪生兄弟,过早地把家安在莘莘学子的心灵上,它们越长大,学子们的心理负担就越重。连乌去纱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他快乐的源泉竟只剩下了楼上那双眼睛。
演讲比赛改变了很多东西,唯一没有改变的是那双眼睛。同样的时候,她依旧出现在老地方,依旧目不转睛地望着乌去纱,也依旧是那么静如止水,波澜不惊。在那双眼睛看来,似乎没有过什么演讲比赛,更甭提什么演讲比赛的第一名,乌去纱和虚空仍然没有区别。不行,既然进入了那片视野,就要想办法摸清它的底细,抢占它的制高点。否则,即便考进北大,也算不得多大的胜利。
乌去纱放下演讲比赛冠军的架子,开始去寻找那双眼睛。不是寻找它的位置,它的位置早在那里,而是去寻找它里面的风景。在学业上风光无限的乌去纱,试图表现他在另一个领域的探险精神。当然,他不是一个盲目冲动的人,不是一个舍本逐末的人,更不是一个不懂得“欲速则不达”道理的人。他长时间和那双眼睛对视,尽量把自己的目光修炼得柔润、和悦,收敛锋芒,不让它惊吓了对方,从而使得对视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整个课间,他们就这样对视着,谁也没有挪开过一眼。最大的干扰来自于邱雁雁。她认识乌去纱之后,时常在楼上肆无忌惮地对着乌去纱傻笑,一笑弯腰就把手搭在吴盈盈的肩上。他不得不将视线从吴盈盈身上移开,去应付一下邱雁雁。有一次,邱雁雁向他挥手,手在吴盈盈眼前摆来摆去,那样子仿佛在给楼下的乌去纱测视力。
楼上那双眼睛已被乌去纱纳入他的日常生活,成为和书本、钢笔、眼镜、一日三餐等并驾齐驱的重要事物之一。长时间的对视并没有增添他的烦恼,也没有让他产生对视之外的欲念。双方皆安然于这样一种情境,简单地走进与走出,没有多余动作,没有言语,没有交流,没有互相影响,谁也不放弃,谁也不发力,谁也不得寸进尺,谁也不把对方当作负担。
有天傍晚,值班的乌去纱从学校开水房提着一桶开水出来,刚到食堂的拐角处转弯,见邱雁雁挽着吴盈盈的胳膊,有说有笑地走过来。满桶开水很沉,乌去纱生怕水在行进途中从桶里荡出来,所以不得不把提开水桶的那只手往外伸。伸得不够,容易烫伤脚;伸得太多则需要更大的力气。乌去纱显然不是力量型的,他只得斜着身子,以此降低自己的重心。还没转弯时,他听到一阵豪爽的女生笑声,很像邱雁雁的。他预感到机会可能来了。甫一转弯,他很自然地抬起头来,招牌式微笑正好与邱雁雁和吴盈盈打上照面。邱雁雁连忙向他挥手,讨厌地遮住了吴盈盈半边脸。邱雁雁的手总算落下了,乌去纱头一遭近距离观赏吴盈盈。她也看着他,似笑非笑。准确地说,应该是没有笑,“似笑”是乌去纱渴望的眼神虚构出来的。但那双乌黑闪亮的眼睛给予了他更大的震撼,仿佛传递出一种明净的忧伤,又像是无声的求援——肯定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我,只是我没有听到;或者,我听到了它的召唤,只是它没有发出声音。她们一晃就过去了。乌去纱站在那里,刚欲回头,这时一个男生猛冲过来,狠狠撞着了乌去纱提水的手肘。乌去纱后退两步,也没能止住荡出来的开水泼在他的右脚上。
他坚持把开水送到班上,才去医务室上药。右脚背中部起了很多水泡,红得像透明的胡萝卜。医生用清水冲洗后,上了烫伤膏,再用药棉和胶布把创面保护起来,嘱咐乌去纱一周之内不要下水,尽量少走动,每天到医务室换一次药。乌去纱被开水烫伤的消息惊动了班上和学校,歪脖子班主任非常着急,乌去纱是今年高考的最大希望,现在正是复习的关键时期,要是受伤影响了状态,如何得了!学校紧急派医务人员去县城进最好的药,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让乌去纱恢复健康。歪脖子班主任专门组织了一支看护小队,一天到晚不离乌去纱左右,帮他穿衣、打饭、洗脸,从寝室背到教室,从教室又背到寝室。乌去纱觉得自己没有伤到那个程度,无须麻烦这么多同学,但歪脖子班主任不容分说,两眼一瞪,乌去纱只得乖乖就范。
课余不能出去。那双眼睛还在楼上吗?我不出去,她会望着谁呢?她到底是望着我,还是望着某个地方?这个问题让乌去纱颇感焦虑,他把唐宏伟叫来,要他出去看看。不一会儿,唐宏伟猫着腰像个探子进来报告:“没有。外面没看见她。”乌去纱心里窃喜,脚虽然痛着,内心却有一种少见的安宁与快慰。
烫伤没有想象的容易对付。上了两三天药,伤口不仅未见好转,还有化脓的迹象。医务室、教务处和歪脖子班主任三方会诊,决定给他打消炎针。乌去纱小时候最怕打针,他没生过大病,但每次打过预防针之后他都要病一场,他妈说他是哭病的。好多年没被针欺负过了,听说要打针乌去纱坚决反对,他说,宁愿加量吃药,千万不能打针,那会让他出丑。歪脖子班主任喝道:“药怎么能随便加量吃,你不要命啊?打针!”乌去纱对着医务室的天花板喊道:“不要命了我也不打针!”任凭歪脖子班主任瞪得眼珠子都快爆出来了。这时,校长进来了,他耐心细致地给乌去纱做起思想工作,从国家的高考政策到个人的前途命运,从学校的战略发展到班集体的无上荣誉,还搬来了关云长刮骨疗伤的故事。他说:“我们医务室这位老医生,有着十多年医疗经验,一生治病无数。他是我们学校的华佗,你不相信他还相信谁呢?来,老胡,我亲自做你的帮手。小乌不会有问题的。”老胡就是校长说的“我们学校的华佗”。乌去纱听校长这么一说,喊也喊不出声了,愣愣地钉在那张板凳上,好像糨糊把屁股粘住了。校长起身,捉住乌去纱的胳膊肘,一边招呼老胡,他正在用一块小磁片切割装着药水的小玻璃瓶:“老胡,得拿出你的最高水平,这可是我们学校的优等生,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痛不能痛优等生啊!”
老胡用磁片围着玻璃瓶的“脖子”划了两圈,拿起一把镊子对着玻璃瓶细长的“脑袋”挥手一击,再用针尖把瓶里的药水全部吸到针管里。乌去纱不情愿地解开裤带,老胡一手握着针管,一手捏着两根棉签,其中一根蘸着紫红色的碘酒,一根蘸着白色的酒精。他气定神闲地向乌去纱走来,乌去纱浑身的肌肉一阵紧似一阵。校长连连说:“放松,放松。”老胡用力把乌去纱的裤子往下扯,乌去纱则用力往上提。老胡说:“打哪里呢?打在裤子上啊!”校长也扯了一把,乌去纱便卸了点力,露出像银元一般白白的屁股。屁股某处突然凉了一下,肌肉立马收紧。老胡说:“打不进去呢,硬得像砣铁!打支针又不是剖腹做手术!”校长故意唬着脸说:“乌去纱你不像男子汉,打个针怕成这样,以后讨个老婆不成缩头乌龟了。”话未说完,自己哈哈大笑,老胡和乌去纱跟着哈哈大笑。笑着笑着,一只蚊子莫明其妙地咬了乌去纱一口。还是春天,哪里来的蚊子呢?笑声刚结束,老胡把拆下的针尖扔进酒精盒里。校长问:“打完了?”老胡答:“打完了。”然后得意地问乌去纱:“不痛吧?”乌去纱羞愧地摇摇头,将裤子拽上来,这时他才觉得刚才蚊子咬的地方涌出一股异样的胀痛。
打针确实见效快。脚背上已经化开的脓液迅速收住腐败的步伐,红肿渐渐消退。一周之后,乌去纱勉强能把脚塞进鞋子里,慢慢吞吞地挪动着,看护小队就宣布解散了。更多的时候,乌去纱坐在教室里休息,他不想让吴盈盈看到他一瘸一拐的样子。唐宏伟告诉他,吴盈盈这几天又出现在老地方,她看上去不太高兴,待一会就走了,好像在等什么人。乌去纱决定出去看看,受伤的样子说不定更能引起她的注意呢,他想。他尽量把“瘸”的姿态做得优雅一点。他看过一本书,上面说英国诗人拜伦天生是个瘸子,可人家风度翩翩,才华横溢,随便勾勾小指头就能让贵妇人前仆后继。所以,瘸腿走出去面对吴盈盈的眼睛,才是对他风度的最大考验。
乌去纱从后门跨出教室的一刹那,心头生起一种近乎英雄末路的悲壮感。这种悲壮感让他的瘸腿略显夸张,却及时武装了他的内心。灵魂的强大与精神的优雅修饰了乌去纱的跛姿,虽然这种强大与优雅是多么空洞,但在一种强力意志的控制下,它们短暂地聚结在一起,有效提升了乌去纱的气质。站在玉兰树下的乌去纱俨然一个拜伦再世,他的目光里平添一股孤傲之气,良久还沉浸在对自己气质的回味里,没有把目光送到楼上去。他背对教学楼,望着生出青苔的坡壁,或者,望着虚空。他现在成了那只从天空降落的瘸腿飞鸟,吴盈盈会在上面看他吗?他用背感受着后面的动静,他在背后的喧嚣中寻找一个与他交汇的点。当真切地感受到这个点时,他使着瘸腿,在地上像弹奏一曲美妙旋律一样运转着自己的身体。刚与楼上的眼睛对视,他就明白了自己判断的错误。那双平静而富有穿透力的眼睛告诉他,在乌去纱站到玉兰树下之前,她就已经在老地方安置好了自己的眼睛。也就是说,她是看着乌去纱一瘸一拐走到玉兰树下的,她目睹了事情的全过程。
她的目光里多了些惊讶,她大概还不知道他被烫伤的事。邱雁雁没在旁边,他得以专注地看着她,但看不出明显的变化,连刚才那眼神里的惊讶,乌去纱都觉得可能是他的错觉。他很想走进那双眼睛里去,体会那里的单纯、静穆和忧伤。他发觉,他一直在与一扇虚掩的门对视,门里的人能看到他的全部,他却什么都看不到。
他从没上过二楼。在这所中学里读了近三年书,他没机会也没想过要上去看看。一直以来,教学楼二楼与他没有任何关系。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不是男生与女生的距离,而是高三与高二的距离,是通向高考独木桥的距离。他已经站在桥头了,隔着狂波恶浪,遥望人声鼎沸、扑朔迷离的对岸。
两个月后,乌去纱走过独木桥抵达了对岸。他到达对岸时伤心欲绝,因为他接到的不是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是来自本省的湘江师范大学的召唤。每个人都认定他是要进北大的。在他们眼里,他早已是北大的人,好比同居的未婚男女,只缺一张纸来作证明。可是,偏偏众望所归的事情出现了差池,他离北大录取线差2分。
这2分是一道天堑,让他整整推迟十年走进北大校园,而且只能作为一名普通游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