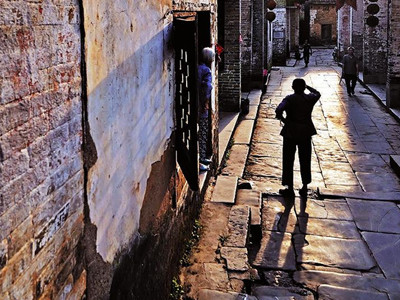
佛心母亲
文丨凌鹰
一
我是被母亲哭活的。
12岁那年,我患了脑病,在离家10余里的一家小镇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而其中的18天,我一直就处于昏死状态。
在我昏迷不醒靠输液维系生命的18个日日夜夜,母亲始终守候在我的床头泪流不止。由于怕影响其它病人,母亲只能像堵塞决堤的河水一样极力压抑自己的哭声和悲伤,因而那哭音便像一股寒冬冰封下的暗流,在母亲破碎的心灵里洄漩冲击。当我从一个很遥远很幽冥的地方摇摇晃晃地走回来时,我睁开眼睛看到母亲正在一颗一颗地掉泪。母亲似乎根本没料到我这时会突然重新张开眼睛。母亲更无法解读这种生命奇迹产生的因果。在某种意义上,因果是一句佛语。可母亲对我奇迹般的死里逃生却有她独有的理解,她将我这种生命奇迹看作是她和我父亲前世做多了善事。我没有用任何医学方面的大道理对母亲解释这种现象。我不愿破坏母亲理解生命与死亡的那种朴素心情。
二
由于父亲只会养鱼,只会做生意,不会干农活,生产队需要男人干的活,就分派给我母亲,母亲知道那些男人们是故意刁难我父亲的,也不做任何分辨,只好坦然的参与到那些男人中去,和他们干同样的活。每次车水,母亲收工时总是抢着去背水车。一丈多长的水车压在并不高大的母亲身上,压得我母亲勾头弯腰,走路趔趔趄趄的,一些妇女见了就埋怨那些男人。我母亲却不以为然的说,这是我帮我自己男人背的,不怪他们。我不知道,面对母亲这份宽容和隐忍,那些男人们是否有过内疚和羞愧。但我知道,母亲用她瘦小而又坚韧的身子与内心,彻底征服了那些自私的男人们。
也正因了母亲这股倔强和韧劲,母亲“吃”的工分同队里的男劳力一样高。母亲用眼泪把我哭活,然后她又用一个女人特有的顽强支撑着我们那个穷困的家。而在这段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里,母亲却没流过一滴泪。母亲每天只管与队里的男人女人们一起出工一起收工,劳动时非常卖力,且一言不发,显得十分地沉静。母亲只想在这份沉默中以她的勤劳多换取一些工分多挣几粒粮食喂养我们几位兄弟姐妹。母亲在劳动中的那分沉寂默然常常令我想到年年月月周而复始地敲击木鱼的佛。母亲就以那样一颗博大的佛心,包容着一切不公和刁难,化解了我们一家生活中许许多多的风风雨雨。
三
善良是每个母亲的天性。
我母亲的善良有时候却让我都有点难以接受。
那时候,叫花子特别多,几乎每天都有一两个出现在我们家门口。尽管当时我们家口粮很紧张,每年都要少半年粮食,但是,只要母亲见到这些叫花子,就会给他们一碗米。如果我们家正在吃饭来了叫花子,她会主动装一碗饭菜倒进他们的碗里,而且也不像其他家那样马上嫌恶地把他们赶走,而是端一张凳子让他们坐在我家门口,让他们好好把饭吃完。然后,还要问一句:吃饱了没有?没吃饱再给你添点。人心都是肉长的,那些一时落魄的叫花子心里是知道我母亲的好心肠的,于是就赶紧起身向我母亲道谢,双眼里闪着泪光。
还有很多手艺人,也经常被我母亲留下来吃饭。他们都是一些补锅的,补箩筐的,补蓑衣的,卖小货的。只要他们到了吃饭的时候还在我们村里忙活着自己的小手艺和小生意,我母亲就会跟我父亲商量,留下他们在我家吃饭。父亲自己就是一个生意人,他在外面走村走村窜户叫卖他的育苗,就经常被人留在家里吃饭。用他的话说,做生意的人,是吃百家饭的。所以,对我母亲的提议,他们从不反对。遇上能喝酒的生意人,父亲还会陪他们喝酒,好想来的不是一个陌生的生意人,而是我们家一个亲戚。往往就这样,那些生意人最后就成了父亲的朋友,然后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母亲居然还放走了一个小偷。
那是一个在我们生产队偷稻谷的男人,小偷是在刚天黑的时候被当场抓住的。几个男人将这个小偷捆绑在一棵枣子树上,然后对他拳打脚踢。我母亲想劝阻那些打小偷的男人们,却被推得远远的,还被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那时候已是深秋,天气已有些寒冷。生产队那些男人们打算第二天将这个倒霉透顶的小偷送到公社去的。我记得我们那个公社有间专门关小偷的房子,他们也想叫这个小偷在那个房子里关几天。
深夜时分,母亲跟父亲商量,想放了那个小偷。父亲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没有做声。母亲犹豫了一下,还是坚持要放了小偷,并说,家里有粮有米哪个愿意去做贼啊。父亲说,那就放吧。母亲就悄悄地溜到那棵枣子树边,解开了小偷身上的绳索。母亲的这个举动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被生产队扣掉了半年工分。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半年工分不是一个小损失了,但母亲却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