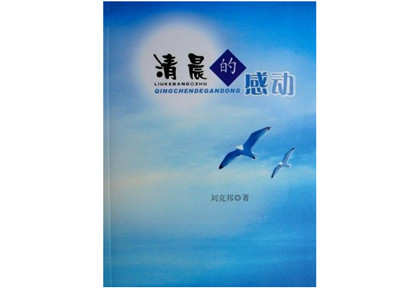
生活褶皱中的一汪深情
——刘克邦《清晨的感动》读后
文丨聂茂
几天前的一个清晨,大约才七点钟的样子,我突然收到一条短信,一看是克邦兄的。他说,他的第二本散文集《清晨的感动》即将付梓,想请我作序。我没有犹豫,欣然应允。但答应下来后,便感到自己有些莽撞,克邦兄与文坛上的诸多名家如谭谈、唐浩明、龚政文、水运宪、蔡测海等交往颇深,我岂能在此班门弄斧?转念一想,克邦兄大约希望我作为一个专业性读者谈谈自己对他作品的真切感受吧。既如此,也就不再顾忌什么了。
之前,我读过克邦兄的另一本散文集《金秋的礼物》,很惊叹于他对生活有那么细腻真切的心理感受,对于过去,对于自己周围的人和事,他总能怀着一种坦然淡定的心态去面对、去追忆,对于生活中普通的一草一木总能发现其中的闪光点,这样的温润心态支配着他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的散文佳作。
当然,我宁愿把克邦兄的散文作品当作这种人生态度的附属品,人生的宽度和厚度决定了文字的境界。克邦兄的文字是纯净而凝练的,这种纯净经过了时间的洗礼,经过了苦难的磨练,当然也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他的青少年时代从文革开始,时代风雨的变幻无常和残酷际遇的刷洗使他的人生路程经历了巨大的潮起潮落,同学、好友、亲人的命运大多在这段时间里都有了跌宕起伏的变化。
克邦兄文字带来的感动也有一些好像与时代无关,完全是一种人性的礼赞。例如,少年同学廖传丰在克邦不慎落水时挺身相救,后又在水库工地为挽救别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人性的壮美深深地印记在他的脑海,震撼着他的心灵,在那段如诗如画的岁月里,廖传丰曾经是他奔跑中的标尺,后来又结下了纯真无暇的友谊,而今,面对差一点吞没他身体的堤岸,流水还在,斯人已去,怎不令人鼻酸泣下?
值得一提的是,读克邦兄的散文,我们既看不到狂风暴雨的时代背影,也有没有情绪上的大起大落,这种在节制感上恰到好处的把握显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繁华褪尽的深沉,百花竟放之后,落英满地,化成了这本《清晨的感动》,灾难的残忍和时代的无情并没有在回忆中成为主色调,生命中的遗憾、美丽、无奈和宽容在克邦兄的散文中若隐若现地散发出来。这就好比不同人生阶段的人穿衣服,年轻人的衣服上经常会有很多的饰品和花样,或者做出不同于常人的所谓个性化点缀,但是,成熟之后,衣服常常会中规中矩、趋于平淡,不会在穿着上追赶新潮以吸引别人的眼球,但是西装和衬衣的美感不会因为少了别出心裁而削弱,相反会因为成熟、庄重、自信而飘逸、洒脱。
读克邦兄的散文,适合在窗明几净的房间里,选择一个无风雨也无晴丽的下午,慢慢品读。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来说,当一天的喧嚣沉静下来,平坐床榻之上,开启温馨灯光,伴随着轻轻翻动书页的声音,进入那个在文字中轻轻流淌出的世界。这样说是因为,年少时的轻狂完全淡去的时候,才意识到,克邦兄散文开启的是一个洗尽铅华的人生空间,这并不是一种崭新的审美范式。但是,在我们当下的散文创作中,却是一个相对稀少的品类,毕竟,年少的单纯难免幼稚,天命之年的平淡必然啰嗦,克邦兄的散文填补了两者之间的空白地带,契合了散文写作的审美原则:从生活的肌理走进灵魂的旷野。
克邦兄是学会计出身,每天和各种各样的数据、表格打交道,在我认识他之前,认为他肯定是一个严谨得近于刻板的人,因为职业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如果有足够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就能从一个人的性格中窥测出他的职业,同样也能从职业中推断出性格的大致轮廓。所以,当我看到《清晨的感动》时,心生疑惑,为什么克邦兄会有如此迥然不同的两幅笔墨?一面是严谨科学,不容许有一丝一毫、一分一厘的偏差;另一面是文字中的诗意人生,富于创新的质感和审美的弹性张力,从“五彩人生”至“旅美日记”,再到“有感而发”,直到最后一页书稿翻过,我的这种疑惑也终于悄然释解。
原因在于,生活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在各个领域中,数字是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文字也是对生活的一种解读,散文就是克邦兄解读生活的一个通道,一种精神表达,一种心灵的追寻,但是很多作家刻意地忽略了生活与散文的距离尺度。
散文与生活的距离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尺度才是合适的?有时,我们的散文离生活太远,口号的罗列在喧嚣过后迅速离开时代的文学中心,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之中,甚至没有“边缘化的趋势”这样一个常见的发展过程;被称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散文三大家的杨朔、秦牧和刘白羽创造了散文写作的模块,关键之时峰回路转,然后柳暗花明;想要赞扬就先厌恶,然后虚晃一枪,是所谓欲扬先抑。这些套路曾经盛极一时,夸张、煽情的语势把读者卷进滚滚洪流,在语流裹挟下完成阅读的暂时快感后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就像跟着上街游行的队伍走了一圈一样,情绪高昂却不知所以。
有时散文离生活又太近,近得与生活没有了距离,零距离的接触被作为原生态的生活加以渲染,似乎生活中的一切都和浴缸结下了不解之缘,浴缸中的感觉被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协的性质是亦官亦民,这样,以写作为业的作家们常常在写作的套模中来回游走,与生活的关系变得很尴尬,生活不再是身边的一切,而是采风和戏讽的对象,生活与写作不再是水乳交融的一体,而是真正的“表现对象”,是写作的“他者”。
克邦兄的散文把目光放在身边的生活中,不去讲述那些与哲学已经难分难解的深奥道理,不在遥远的历史纸堆中低首徘徊,也不沉迷于历史遗迹的凭吊,他无需刻意地去挖掘什么写作资源,写作只是一种惬意的人生表达,这从他的《我的生活不能没有她》、《老处长》中都可以看出。正如冯伟林在《温润的素描》中所说,“对他来说,写作不是职业,更不是谋生的手段,所以就少了一份限制,多了一份洒脱;少了一些功利,多了几分从容。”身边的生活就是一座富矿,其实,写作并不是作家的专利,很多时候,经典的作品是那些文学票友写出来的。
当散文走向名山大川,走进闺房阁楼,走进历史的纸堆,就是不能走近我们身边的生活,不能触摸生命中的灵魂,我们散文的写作现状经常不是离我们的生活太远,远得没有了人间烟火的味道,就是离得太近,近得超越了文学的表现限度。这个时候,票友散文写作似一股清风吹皱了文坛的一池春水。国外没有我们国家类似作协这类的组织,也没有专业的作家,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的专业水准要高过其它国家,我们的文学所体现出的力度和深度与西方文学对比就有优势。事实情况是,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平台上,我们的记录仍然是一片空白(2000年高行键意外获奖,中国政府不承认,而且他是流亡过程中获奖的,代表法兰西民族,似乎与真正意义上汉语作家的获奖挂不上边)。也许我们会说,诺贝尔文学奖怎么能作为评判一个国家文学成就的尺度呢?这个奖的清单上难道就没有次品?所有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可以进入世界文学史的序列?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现状和取得的成绩就连我们自己都不能满意,作品经典化的问题虽然屡次的被提出来,但是哪些作品去挑起经典化的重任?哪些作品众望所归地构建一个当代文学的殿堂,一直没有!我们讨论的问题是,票友写作是否是我们散文创作中的一种有益补充或者改变格局的力量呢?
读克邦兄的散文有时会有直刺内心的力量。《少年同学廖传丰》,让我想起卢梭的《忏悔录》,每个人在群体中展现出来的只是一些点的组合,都会以光鲜的面貌出现,当然这也是一种美德,体现了对别人的尊重。但是,作为本能,很多人对于过去的一切会有一个筛选,选取那些值得回忆的东西在脑海当中反复再现,言谈中也会得意于那些辉煌荣耀的往昔岁月,甚至点点滴滴都能准确地出现在该出现的场合、该出现的位置。
实际上,那些不堪回首的伤疤在记忆中才有更深的刻痕,灵魂深处的内心世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透明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禁区,这个禁区不容许任何人去触碰,包括自己,多数人在提及自己的那一片心理禁区时会刻意的回避,纵然如此,我们也会表示理解,毕竟这是人性使然,自我解剖的精神和勇气少之又少,在《忏悔录》中,卢梭对少年时代因为无知和狂妄而犯下的错误做了毫无顾忌的坦白,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新型人格之美。后来读到巴金的《随想录》,对于在文革中自己没有勇气站出来捍卫正义和真理而感到深深的遗憾,甚至是歉疚和惭愧,巴金没有找任何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在克邦兄这里,首先是强烈的自我解剖精神,这是一个真正有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精神,在细微之处,通过儿时的一段往事,回到生活的深处,作者没用任何华丽的词语和句式,文本中的“我”(实实在在的作者本人)和廖传丰因为交往中的普通小事,罗盘的丢失导致我们之间产生了摩擦和矛盾,后来,时代的大潮把每一个人卷起,而后放置在了不同的海滩之上,“我”在长沙,他在湘西。多年以后,当“我”再次回到湘西,面对似曾相识却已经今非昔比的家乡,面对自己遇险而被廖传丰救起的那个堤岸,思绪随着罗盘回到那个遥远的从前……,无需宏词大调,无需煽情夸张,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真切,这种自我深情的回忆,我们不会感到丝毫做作和伪饰,还有一种童趣丧失之后的伤感之美。
克邦兄尽管是一个政府部门的领导干部,但是,从骨子里讲,他仍然觉得自己是众多普通百姓当中的一个,没有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这是一种朴实的平民情怀,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一个知识分子,克邦兄的心理基点从来都放在普通的百姓之上,像他这样级别的官员,完全可以利用一些便捷的资源来解决身边生活中的问题。《门诊遭遇记》中的克邦兄不再是那个在办公室中伏案沉思的领导,去掉了身份头衔,离开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到了医院里,他就只是一个普通的患者,这就如同将军和士兵脱了衣服,跳到澡堂子里边,大家都一样,肩章上的繁复图案所代表的身份符号被完全拆解。在医院排队、挂号,等护士叫,然后才能一睹医生真颜的过程是非常艰苦的,因为每一个在焦虑和无奈中等待的患者都抱着同样的期待,希望医生的一纸处方能够成为切除病痛的利剑,希望用那些白色的药片和倒挂的液体瓶去抚慰漫漫长夜中呻吟的灵魂。
这种经历和心态如果不是亲身感受,很难在生活和工作中贯彻“以人为本”,所有的呐喊都只是口号。正因为此,我觉得克邦兄的散文虽然没有鸿篇巨制,但它的意义都有着别一样的重量,它的风景有着别一样的美丽。
感谢克邦兄的信任,使我有幸成为这本散文集的第一个读者,对此,我深深感动,并向他祝福。
作者:聂茂,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