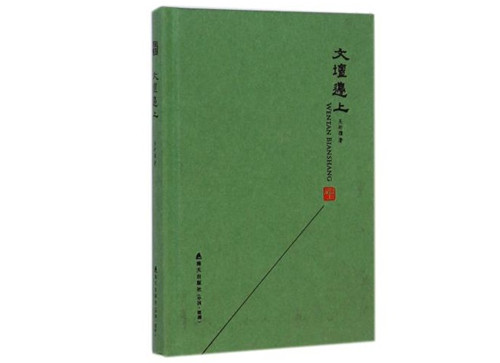
文坛边上·2012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6月26日 阴 星期二
《中国工人》杂志第6期,胡宏梅女士责编的“工人心声”专栏看出了我的泪水。这个专栏只有一篇文章:李大君先生采写的《大工地诗歌节——建造建造者的尊严》。说的是,“2012年5月1日,公益组织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与劳工志愿服务组织安全帽志愿服务队在北京举办了一场专门以建筑业农民工为主题的大工地诗歌节”。这段话不容易读顺,简单地说,就是某公益组织在北京为建筑业农民工组织了一场诗歌朗诵会。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建筑本就是一首凝固的诗,建筑业农民工理所当然都是才华出众的诗人。何况,在当下中国,他们集最尴尬的身份、最辛劳的工作、最割舍不下的乡愁于一身,他们的诗歌作品,不是“积劳成句”,便是“蚌病成珠”。
山东建筑工友王运朋有一首自嘲诗写道:“冷眼斜视是世风,莫道不与往日同。自慰身份得巨变,盲流变成农民工。”
工友释蒿的《暮归》颇有晚唐风范:“日落暮色浓,收工归帐蓬。风来知了乱,草里蟋蟀鸣。悠悠胡琴荡,渐渐同乡逢。谈唱不知时,衣衫觉露重。”
最让我震撼的是河北工友谢仲成的长诗《冷眼》,不惜全部摘录如下:
“经济已成鸦片,金钱蒙蔽双眼,阶级已经淡忘,斗争已成笑谈,一切向钱,向钱。
“剥削的人有了原野沃土,生活的糜烂成为他们的乐园,宽松的环境使他们得意忘形。公开和社会叫板,他们可以张牙舞爪,他们可以肆无忌惮。他们露出的是狰狞的嘴脸,他们干的是伤天害理。他们可以对劳者说:想干就干,不干滚蛋!榨取你们的血汗应该,完工欠薪理所当然。弱者无理可讲,屈者何处申冤,又有哪个敢讨要工钱。看朱门酒肉,有谁知背后隐藏多少辛酸?
“严峻的形势不容乐观,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为平等我们必须斗争,为解放我们应该奋战,我们决不允许剥削死灰复燃,我们的呐喊,一定要让剥削者闻风丧胆。朗朗乾坤岂容黑暗,历史车轮怎能倒转,劳动者的飓风行动,既能拨云见日,亦能将世界改变。”
这是大工地诗歌节为社会、为政府、为民众提供的另一种独特的诗歌文本。在这些文本中,建造了无数高楼大厦、楼堂馆所的农民工们,试图建造另一种更具永恒价值的东西——平等与尊严——除了向老板讨要工钱,他们更想努力向这个社会讨要完整的工人身份和公民权利。
他们,能得到吗?李大君文章的结尾一句是:“总有一天,一切颠倒了的,必被颠倒回来。”
6月27日 多云 星期三
前天晚上,薛忆沩从深圳到了长沙。昨天上午,我与复生联系,希望《晨报周刊》能对忆沩做一个专访。复生的回答是:薛忆沩的专访焉能不做!他还在QQ上发来我在2006年6月24日《晨报周刊》写的“昕孺的书籍”,我推荐了三本书,第一本就是薛忆沩的短篇小说集《流动的房间》。
复生安排在曙光北路的pagel咖啡馆招待忆沩。忆沩上午10点多到我办公室,他聊了在深圳的一些文学活动,我看到特区报、《晶报》、《蛇口通信报》等对他新书出版做的专访与大幅报道。这个一直被边缘化的“异类”终于修成正果。
11点多,三湘都市报编辑李婷婷过来。她写的《薛忆沩:用语言和想象,带我们去看不见的城市》,忆沩很满意。但三湘都市报的《都市周刊》在发表时限于篇幅,作了比较大的删改。婷婷在专访中提到薛忆沩讲的一次很有意思的经历:
“有一次我去看一个很有名的话剧《推销员之死》,那是首演,亚瑟·米勒自己导演的。我在那里等着买票,突然一个老外给了我一张票,我进去坐下后发现,我前面坐着曹禺先生,旁边坐着丁玲女士。当时位子很空,我的整个这一排都只有我和丁玲两个人,当时我还和丁玲聊起了长沙。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种氛围给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带来了很大的触动。”
我相信,这样的人生奇遇对一个人未来的走向,其意义不可估量。或者迷信一点地说,这就是一种天意。
12点,敏华开车,带忆沩、婷婷和我同赴pagel咖啡馆,与复生,还有《晨报周刊》的记者孙魁、李林冬见面。复生是第一次见忆沩,但06年通过我的书籍介绍,他对忆沩心仪已久。因此,他现场称我为“文学酵父”。孙魁是《晨报周刊》的名记者,才知道他是山东人,因为喜欢南方留在长沙。李林冬是摄影记者,曾到过我办公室将我发展成为他的模特;他一见到忆沩,就色迷迷地眉开眼笑,眯起一只眼睛对着他“咔嚓”个不停。
我跟忆沩聊了会读书。我们都喜欢马尔克斯,这个很容易理解,马尔克斯在中国没有阅读障碍。但忆沩最喜欢的西方作家是乔伊斯,他反复提到《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尤利西斯》,这两本书我都没能看得进去。他说,他看的是英文本,语言极为精准、优美。据他所知,《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汉译本也是很不错的。他建议我下决心冲过前面那部分,看到后面就好了。
7月6日 晴 星期五
惠州读书种子周春寄来大著《远去的书声》,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周春的笔名叫周老泉,时常在各类读书报刊上读到他的大作,以为一白发老者,不料却是货真价实的八零后人。他走到哪里,便访书访到哪里,读书读到哪里,文章也写到哪里。其才情与勤奋,均拔萃于同龄人。
“几个歪斜欲倒的旧书架,阡陌纵横的旧书,摊着,像砖瓦厂的砖坯。摊子上方是一棵大榕树,长长的胡须,偶随风动。秋风不时吹落几片枯叶,飘落在书上,惹得挑书者蹙眉摇头,或撮起嘴来吹吹,或腾出手来扇扇,为安静的书摊添出一点气息。”
我喜欢这样的文字,让人动心。读书不能读成书虫,买书不能买成书包,藏书不能藏成书橱。读书,要读出自己的真性情来,让一个本色的我行走于天地之间。读书人应该比普通人对世事有更多的敏锐,而不是更迟钝;对现实有更多的关注,而不是逃避;对场景有更多的体贴,而不是麻木。
读周春这本书,加上之前在《悦读时代》上读到春锦的读书日记,再加上时常读到更多的年轻书友的读书文章与著作,我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不知对不对。说出来也无妨,供朋友们参考。我觉得,时文读得太多,经典接触有限,写出来的文字不能说不好,有清水炊茶的潇洒,有竹影扫阶的淡雅,却很少能看到别开生面甚至苦心孤诣之处。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真正的“远去的书声”。
我想,年轻一代书友们应尽可能减少“书场应酬”,你来我往,宾主互换,那种唱和有意义,意义不大;有意思,意思不多。倘能潜心经典,埋首诗书,说不定哪一天,读书种子就能脱胎换骨,跃然而为读书大师。
周春兄为人赤诚,读书专警,潜质无限,故斗胆陈辞。昕孺才浅,又不能免俗,以吾之不能为之事,责之于年轻人,吾已先面红耳热矣。
7月13日 晴 星期五
本月初,湖南大学文学院倡议的、代表湖湘文化精神的《湖湘九章》评选揭晓,分别是:屈原的《湘君》、贾谊的《鵩鸟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周敦颐的《爱莲说》、米芾的《潇湘八景图诗序》、王夫之的《船山记》、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
这个结果基本上是靠谱的。当然也会有些争议,比如为什么一定要选九章,十章行不行?还有,是不是每人仅限一篇,一个人有两篇行不行?
像屈原,我觉得选《湘君》不如选《离骚》和《天问》。《离骚》是史诗般的作品,是描写湘楚风物和亲民爱国最有代表性的篇章,《天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探究人与世界本源的诗歌,这些都是后来湖湘文化“胸怀天下”、“敢为人先”的源头。
如果范围稍大一些,还应有柳宗元《愚溪诗序》的一席之地,它不太为人所知,却是柳宗元写得最好的小品文,无论文学价值还是思想价值,都不亚于《桃花源记》:“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予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另外,唐代两位大诗人李白、杜甫缺席了。李白的诗中出现“潇湘”的次数极多,他对湖南是很有感情的;杜甫晚年漂泊潭州(长沙古名),最后死在湘江的一条船上。所以,我觉得,李白的《远别离》和杜甫的《发潭州》也是应当考虑的。尤其是李白的《远别离》,比屈原的《湘君》更有说服力,它让潇湘成为忧伤、哀愤的代名词。
7月26日 晴 星期四
死亡似乎是2012年的重大主题。刚从贵州回来,就听说了骇人听闻的“北京大雨”,赶紧发短信给刚去北京工作的彭一笑同学。笑同学说,舅舅你的慰问短信发得也太迟了啊!我说,不是我迟,是雨下得太快了啊!
一场暴雨,让北京死那么多人,真让人不敢相信。但现实往往是由不得你不相信的。
北京市长郭金龙辞职。虽然中国有辞职官员迅速另谋高就的优良传统,但市长辞职依然体现了政府的承担。但愿这种承担不要演变为一种“个人秀”,用个人的职业亏损来为一个效率、效能低下的政府卸责。倘若是这样,那我宁愿相信房山区区长的含泪致歉,我更相信,一个男人的眼泪里面良心与良知的含量。
在北京奥运四周年纪念、伦敦奥运即将开幕之际,这场夺去数十人生命的暴雨,是一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它让我们从城市灾难的背后,看到组织的麻木、社会的怠惰、个人的渺小,以及隐藏在灯红酒绿、繁华富丽中的种种致命杀机。正如笑同学在日记中记载的:“这哪是下雨,分明是下刀子啊!”
是啊,悬在我们头顶的无数刀子,随时可能像雨点般掉落下来。
7月28日 晴 星期六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对奥运会的兴趣便大大降低。通过当一回东道主,中国在国力与体育竞技诸多方面,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实力,现在是应该花精力好好处理内部事务的时候了,否则,北京奥运会有可能成为一朵巨大的昙花。在我看来,伦敦奥运会之前的北京大雨,就是一次这样的警示。
在这样的心理与背景下,便没有起床去看那四点钟的开幕式。连英国都有很多人反对本届奥运会,我们又何必去凑热闹呢!有反对的声音总是好的。奥运会和军备竞赛、能源竞争、核试验一样,在现代社会走向了它的歧途。
中国体育的伟大目标似乎就是为了四年一届的奥运会能拿几十块金牌,与此同时,对国民素质尤其是青少年体质持续下降却束手无策。近视、佝偻、营养不良、心理健康等问题日益突出,对于这些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国计民生”,有哪些部门能拿出明确有力的措施来?体育局组织的球赛还在以大打小,教育部组织的高考依然雄关漫道,质监局大肆提高我国食品的安全标准……最滑稽的是卫生部,最近公然宣称我国已跨入全民医保制度国家行列。且不说,部长先生公布的数字是96%,“全民医保”就要把那4%排除在外吗?为什么不努力工作,继续加把劲,解决那4%之后,再说已跨入全民医保行列呢?其好大喜功的作派,一目了然。关键还不在这里,而是这96%的水分究竟有多少?可以说,我们所谓的全民医保还基本上只是停留在制度层面上的东西,对于目前愈演愈烈的医患关系、愈来愈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愈来愈行政化的医疗机构,都没有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切身问题。
每一个国家都在奥运会的大家庭之中,奥运会的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能让人民更快富裕,拥有更高的幸福指数和更强大的身心力量,这样的国家,才佩得上戴上一块奥运会的金牌。
7月31日 晴 星期二
诗歌在湖南一直不太受到重视。有作家说,湖南最重视的一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二是儿童文学,三是散文和报告文学,四是文学评论,最后才轮得上诗歌。这种说法既有道理,又不太有道理。有道理是因为它是一种客观事实,不太有道理是因为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包括诗歌,都没有理应受到重视一说。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一种个体行为,只有写作主体对此重不重视的问题,企望读者、社会以及某些机构的重视,除非两点:一是它本身有着重大的实用价值,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诗歌对于中国社会思想解放的启蒙,它于是不可思议地红火起来;再比如时下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能给作者、出版商以及当地作协带来巨大的名利效应,因此能引起社会的格外关注。二是它在某个时代达到极高的水准,比如诗歌在唐代、词在宋代、小说在明清两朝,等等,群星灿烂,而且涌现出巨星来,你不重视它都不行。
诗歌在当下,既不实用,又无巨星,欲在时代的大舞台上成为浓墨重彩的主角,宛如白日做梦。然而,这又不代表喜欢诗歌的人少,或者看好诗歌的人少。著名作家谢宗玉把小说、散文、随笔写得出神入化,偶尔弄几句古风应酬一下别人的饭局和山水,基本上不写新诗,但他经常参加湖南诗人举办的各种活动,给湖南诗人们送温暖;入主湖南作家网不久,即大张旗鼓地推出“湖南实力派诗人及其代表作”系列,他对诗歌的一片爱心更是表露无遗。
这个系列出场的第一位诗人是我的偶像匡国泰。国泰兄的诗歌清新、空灵,诗性与智性圆融无碍,他把现代诗写得极具湖湘风格与古典气质,洵为湖南诗歌的旗帜与标杆。我作为第二个出场,就完全不是水平和影响所致,而是宗玉振臂一呼,我交稿最为积极使然。我选的十首所谓代表作分别为:《爱情》《致桠桠》《瘦》《远方》《布达拉宫》《致苇苇之一》《秋天的原野》《采邑》《蝴蝶》《池塘》。我在选择的时候,兼顾自己创作风格与水平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网络阅读的特点,尽量呈上一些可读性较强的作品,不知是否能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