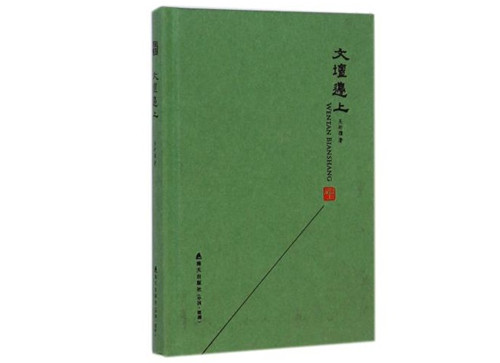
文坛边上·2011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6月2日 阴雨 星期四
《鸟看见我了》是青年小说家阿乙的第二本小说集,收录了他近年创作的十个中短篇小说。蒙远在加拿大的中国作家薛忆沩推荐,此前我对阿乙知之甚少。看简历,他列举的发表其作品的杂志只有三本《今天》《人民文学》和《文学界》,可见也是不太有发表欲或者不是太被重视的作家。
阿乙1976年出生,那一年在中国是很重要的年份,出了很多大事,包括主席、总理、委员长接连去世,唐山大地震死了二十多万人。如此巨大的损失,按照能量守衡定理,老天总是要有所补偿的。阿乙的出生算不算得上一个补偿呢?我不敢说是多大的补偿,但阿乙无疑是1976年生人中的一个亮点。
也许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小说家早慧少,晚成多,当然,青春文学没算在内。很多小说家写到四五十岁才比较成熟。而国外,有些天分高的小说家二十多岁就成名了,比如麦克尤恩。这样看来,阿乙也不算年轻。只是在中国,当看到一位35岁的年轻人能拿出这样的文字和文本,你会感到讶异,读者会感到普遍的讶异。这种反应说明,这位35岁的年轻人或多或少是一个异类。虽然从写作本身来说,他纯正得就像一只盛装小说的优雅瓷器。为什么这么纯正的小说家,在中国看上去是一个异类呢?中国另一个纯正的小说家薛忆沩在温哥华,在异乡。异而不是同,冲突而不是和谐,大约是所有纯正小说家的宿命。他们在和谐社会就成了异类,当故乡被格式化和模式化,他们只好奔赴异乡。
阿乙当过警察,做过国家机器中的一枚螺丝钉。做螺丝钉的经历,让他了解到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状况,这个不难。难的是,阿乙了解了整个国家。他对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细胞组织都洞若观火,不论是威武堂皇的,还是支离腐朽的。作为一名视野独特的小说家,阿乙能敏锐地抓住所有细胞组织的内在联系,不论是高高在上的,还是渺小卑微的。
6月3日 阴 星期五
前天,西藏诗人李素平偕夫人一起从老家四川达州抵长沙。素平夫妇是去江西吉安看望在那里读大学的儿子,听说火车要路过长沙,临时决定在长沙下车看看我,并亲自赠我诗集《拉萨印象》,前面有我的小序《拉萨的天空,弥漫着诗一样的传奇》。诗集由华文出版社出版。
前天晚上,我带素平夫妇去长沙古街太平街,在火宫殿吃长沙小吃,游湘江风光带,见识长沙的市民生活。他们在那里邂逅一群四川老乡,其中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无家无室,在外流浪了五十多年。他们慷慨解囊,对老人予以资助。
昨天上午有会,下午要排练,便挤出中间一段时间,从十点到十四点半,先去岳麓书院和爱晚亭。感谢肖永明教授赠给素平夫妇《岳麓书院史话》。然后,从河西直接乘车到博物馆,拜见2200多年前的利苍夫人辛追。素平兄对辛追的评价是:漂亮。最后,我们到烈士公园年嘉湖边坐了会。接下来,夫妇俩将去韶山和张家界。
6月7日 晴 星期二
《巨流河》在大陆很有影响。此前,好友郑艳、耀红均跟我提到过,郑艳在去美国的飞机上还读着它。所以,我便买了一本三联版的来读。这本书的可读性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作者齐邦媛经历十分丰富,人生跌宕起伏,跨越数个时代;二是齐先生的家庭很不一般,父亲乃东北地下抗日的组织者,一直活跃在国民党的上层,所见所闻更具史料价值;三是齐先生本人是朱光潜、吴宓的高足,学养深厚,文笔清新。
从日军侵华,到两岸融冰,这一段时间跨度不算很长,却异常具有文化与精神含量的历史,本来极具书写意义。奇怪的是,中国作家很少有人能够深刻而全面地去提及它。我相信,有齐邦媛这样经历、身份与思考的,不乏人在,为什么如此激流汹涌的历史,我们只看到《巨流河》(齐邦媛)、《大江大海》(龙应台)这样可怜巴巴的几个文本呢?
还有一个奇怪现象是,综合大陆的情况来看,再加上《洗澡》的作者杨绛、《思痛录》的作者韦君宜、《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两岸作家中,通过个人亲身经历来书写历史的,并写得入丝入扣、感人肺腑的,竟然大多是女作家!
这几位女作家都写得好,至少她们自己做到了最好,她们的作品靠细腻的感性赢得可读性,靠琐屑的往事赢得真实感。反过来,从文本价值而言,这些作品也失之于感性和琐屑,缺少血性和力量。
6月8日 晴 星期三
昨天高考,作文题受到各方关注。湖南的作文题是:某歌手第一句话由“大家好,我来了”变为“谢谢大家,你们来了”。以此为意,自拟题目写一篇作文。这个材料题想法还是不错的,学生的写作空间也较大,可以写社会风气的变化,也可以写歌手素质的提高;可以写“我”与“大家”的关系,也可以谈做人处世的法则。
其实高考作文题无所谓好与不好,对每一个考生来说,好与不好都是公平的。但愚以为,高考作文题应尽量脱离应试作文的窠臼,考出学生的素质与灵气,不要让那些考前大肆背诵材料的考生得逞。
6月13日 多云 星期一
诗人李晃从深圳寄来《湖南青年诗选》和《李晃短诗选》。想起大半年前,李晃邀请我担任《湖南青年诗选》编委时,我虽兴奋莫名,倾力相助,但一直担心着,以一己之力编一本时空跨度如此之大的诗集,能否拿得下来。如今,沉甸甸的诗集捧在我手里,给予我的是此前难以想象的惊喜。可以说,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完备的湖南诗人选本,从50后到80后,时间跨度整整四十年;地域不仅囊括湖南14个地市,而且将遍及全国甚至国外的优秀湖南籍中青年诗人,几乎一网打尽。
我没见过李晃,但到过他的老家隆回。没去过时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近代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魏源会是隆回人?为什么隆回拥有新时期以来湖南最大的一个诗人群体?到了那里,我才明白,隆回高山峻岭、林茂水幽,没有一条很宽的路,却到处都是可观之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只要稍有文化,便会对家乡的风物人情产生极强的感受力与表现力,更会对外面的世界产生极强的渴望与探究之心。魏源出去,打开了近代中国的视野与胸襟。这不,匡国泰、谭克修、马萧萧、李晃、李傻傻、袁蛟等年轻诗人也出去了,他们既让人看到隆回诗人的性灵才气,更让人感到湖湘文化的厚实底蕴。
如此说来,由隆回籍诗人李晃来完成这部《湖南青年诗选》的主编工作,或许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6月15日 雨 星期三
两个多月前,四川散文家、“在场主义”发起人周闻道先生打电话给我,他主编的《在场》杂志欲从今年夏期起,创办“在场地图”专栏,刊发全国各地符合在场主义理念的散文精品,首先想推出散文基础较好的湖南,盛情邀请我参加,并委托我另组三位散文家的优秀稿件。通过我自己的阅读经验,以及与闻道兄协商,最终确定了岳阳的散文家沈念、邵阳的散文家周伟和长沙的散文家远人。他们分别奉上了自己的力作。
《在场》杂志2011年夏期(总第七期)已经出刊,“在场地图”的湖南散文小辑“主持人语”是我写的,其中也免不了黄婆卖瓜,自夸了一把:
在湖南的散文作家中,沈念、周伟、远人、吴昕孺是特点比较鲜明的四位。
《夜发生》有着近乎小说的述事,却展示出比小说更为练达的自由,沈念的笔头总是挟带着一种尖锐,让我们看到夜晚的深处,在那里所“发生”的一切,比如故事、历史,还有欲望和孤独。
周伟用与泥土极为相近的朴质书写着自己的乡村,《乡村功课》因为怀想而超越了忆旧,无论求雨,还是射尿,周伟的文字始终像田畔的野花一样,绽放得无拘无束。
远人文如其人,永远干净清静得如一片白云,《城市里的鸟鸣》是一篇独特的文字,因为它在喧哗的都市为我们“衔来整整一个自然”。
吴昕孺的写作充满着智性与想象力,《父亲的清明节》在跳宕的文字和奇妙的情节中,给我们展开了一幅乡情与亲情的画卷。
总之,这四位作家通过自己真诚、开敞而又风格卓然的写作,代表性地诠释了在场主义的散文理念。
6月20日 雨 星期一
好友罗争玉荣任华文出版社社长已有一段时日。他将华文出版社解读为:“华文所事,修文载道。激荡文字,论世衡史;涵蓄华章,蕴秀文化。博采众声,广纳雅言;灼灼其华,郁郁乎文。书非千轴,文不百代;气非自华,因人而彰。心系华夏,文名四海。总览人文,化成天下。华文出版,劲风满帆。”此论不唯有经营理念、出版思想,更有历史与人文的担当。
霎那间主人王庭坚从北京发来短信,赠李白诗句“莫道词人无胆气,临行将赠绕朝鞭”与我共析。他说:“中国历史,既是一部草民嚼烂菜根的苦难史,也是一部文人问破苍天的愤懑史,只是文人往往彷徨于忠良之辩,又踟蹰于操守之惑,故酬志者少,抱憾者众……”
我对此的理解是,中国文人往往个人道德感太强,从而压抑并割裂自己的历史使命感。他们往往只看到自己在时下功名册中的位置,而较少追求自己在生命版图中的坐标。
6月30日 阴雨 星期四
廖兄静仁,湖南安化人。益阳安化,层峦叠嶂,山高谷险,自古为匪患马帮之乡,至今犹有茶马古道遗迹。静仁兄怀抱文学,满腹经纶,却一副武貌,长髯粗口,大鼻深目,全不似咬文嚼字之人。上世纪80年代初,以一篇《纤痕》引爆湖南文坛,遂成散文顶尖高手。曾任安化县报总编辑,并成为“湖南省劳动模范”,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搞文学能搞到这个地步,让人匪夷所思。
不久,廖兄来长沙,在省文联主编《财富地理》杂志。我的书架上收藏有十余本《财富地理》,此刊不唯装帧漂亮,印制精美,而且往往一刊一地,将当地人文、风物、气象、资源等一网打尽。这种独特创意既让《财富地理》称闻湖湘,也让廖兄赚得盆满钵满。接着,他创办《自觉》文化杂志,并于捞霞开发区、湘江世纪城等多处开设“自觉”茶厅,广纳湖湘文人骚客。去年,我曾有诗登上《自觉》雅舍,既铭谢廖兄美意,亦深感其包容与活力,为常人所不及。
今年三月,安化美女喻俊仪与我接上头,说廖静仁正在主编《新时期湖南文学作品选》,分为三卷:短篇小说卷、散文随笔卷、现代汉诗卷。邀我加入,我欣然从命。三个月后,三本大部头即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付梓。昨日傍晚,我赴“自觉”茶室拿到样书,果然是大手笔。
拙作,曾刊发于《绿风》诗刊2009年第6期的《十五行诗三首》入选现代汉诗卷,曾刊发于《安徽文学》2008年第1期、并获得当年“安徽文学奖”的《岳麓书院——灵魂的入口》入选散文随笔卷。细读这两卷,均立足于新时期三十年背景,将湖湘视野的宽度与文学经典的高度相结合,具有不菲的史料价值。
7月12日 晴 星期二
读毕云南作家吴安臣的散文集《草从对岸来》,贯穿在我心中的只有一个字:苦。佛教有四谛,苦集灭道,苦字当先。安臣真是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前日,我在饭桌边,向我的家人们讲述安臣的身世,都不禁唏嘘。而我在这样的日志中,真不忍再复述一遍。但离开了那苦,就无法谈文。安臣自幼父母离异,兄妹随母亲从出生地山东回外婆家云南。在云南,母亲再嫁,一家随继父到河南。继父所说的繁华锦绣乡竟是一片盐碱地,穷得无以复加。他跑到山东寻生父,不料生父因意外早已亡故。接下来的是,高考落榜,女友离去,叔叔病逝,小妹妹精神失常,母亲寻短见,岳母遇车祸,自己四处漂泊……这些开中药铺似的罗列,尚不足以道尽个中艰难。70年代出生的安臣,在人生旅程中所遭遇的辛酸和困苦,不亚于经历一次乱世。
其实,所谓人生,就是用理想和情怀来匡扶自己的乱世。
安臣有文学理想,有悲悯之心,因此,在他自己的乱世里,他百感交集却心智超然,彷徨无地却意志坚定。在他的文章中,有无奈的慨叹却没有抱怨,有伤心的忆往却没有追悔。从那些石子般坚硬、明晰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读到安臣那一颗善良、敏感、柔韧的心。这样的苦,往往可以击败一个人,让他变得悭吝、尖刻,仇视他人和社会,但安臣,由于有这样一颗心在,由于有他的理想和情怀,他始终是一位彬彬君子,是一位隐忍、勤奋、富有爱心的写作者。
7月18日 晴 星期一
前些天,接到薛忆沩电话,他从加拿大到了北京。17日上午,他再打电话时,已在长沙河西谷山村舅舅家。十点,我从水木轩出发,先后经过浏阳河桥、捞刀河大桥和三汊矶大桥,进入河西。忆沩在谷山加油站等我。谷山村属岳麓区,与望城县一山之隔。忆沩舅舅家乃一精致大方的农家院落,坐在堂屋边喝茶,边聊天,大有“把酒话桑麻”的味道。
忆沩给我看台湾郭枫先生主编的《新地》文学杂志,上面有他最新长篇小说《白求恩的孩子们》(连载),第6期还刊发了我对他的中短篇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的评论——《惦念是最好的安魂曲》。《白求恩的孩子们》是忆沩用英语写的第一个长篇,然后他自己译成中文,圈内评价极高,但在大陆暂时找不到发表之地。
忆沩谈到在北京,他见到一些新锐小说家,如阿乙、瓦当等,欣喜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学潜质,同时也为他们的写作环境感到担忧。他说,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顶尖水平差距仍然很大,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也比较混乱,但西方文学同仁对中国当代文学有一个共同的疑问,那就是中国的写作者大多止步于四五十岁,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四五十岁现象”。而在西方,一个作家四五十岁要不刚刚成熟,要不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在他们看来,中国写作者特别容易见异思迁,把职位、地位和物质层面(比如获奖)的东西看得太重,把文学反而看得并不重。
我们聊到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我刚读过他的随笔集《作家看人》。我说,奈保尔对诗人沃尔科特的评价不公平,但他的《米格尔大街》实在迷人。忆沩说,奈保尔对英语文学的贡献极大,他改变了英语的质地。英语是一门古老的语言,自莎士比亚以来,英语一直繁富、芜杂、纠结,是奈保尔这样的作家让英语变得简洁、活泼,富有张力。我说,我从《布罗茨基谈话录》中深切感受到移民作家,尤其是流亡作家那种不可救药的孤独感。他说,是的,任何人移居国外都不会像一名作家那样拥有深刻的孤独感,那种孤独感可能伤害到生活,却丰腴了文学。
终于见到忆沩的妈妈和外婆。外婆已是97岁高龄,鹤发童颜,精神饱满。忆沩把我带到老人面前,听她背诵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燕子诗》,都是数十行的长诗,老人吐词清楚,抑扬顿挫,毫无停顿,宛如行云流水。我对忆沩说:“有一天你若成为伟大作家,这里就是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