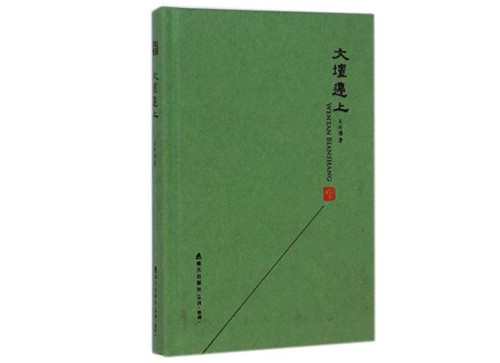
文坛边上·2010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6月1日 阴雨 星期二
晨曦在电话中兴奋地告诉我,他今天上了一堂课,专门讲我的诗歌,讲得兴起,还拖了堂。我说,我很想去旁听的。他就讲了一些他对我诗歌的理解,以及他是如何在课堂上讲解《瘦》这首诗的。他罗列“瘦”可以呈现的几种情状,并问我当初写这首诗的起因。
大概是2006年底,我们大学同学聚会,几位多年未见的女同学说我比以前更瘦了。平时说我瘦的人很多,也没什么触动,女同学的话效果的确不一般,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就是诗一样的句子,回到家里几乎一气呵成。《瘦》这首诗是用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具象,如眼镜、脸、书架、黑色衣服等,来反映我性情中某种抽象的东西,比如骨气、清高以及对自我价值的期许。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首励志诗。
晨曦说,他感觉到我诗歌作品的三个特点,一是生活的幽默,一是语言的刀锋,一是现实的关注。拿他的话说,就是冷不丁对现实生活踢上一脚。应该说,这是我十分认同的好诗标准,是我追求的创作目标。只是目前离这些标准还有不小的差距。我欣赏并采取的写作态度是:慢。
慢慢写吧。坚持,就是快乐。感谢晨曦兄。感谢涉外学院的同学们。
6月18日 晴 星期五
昨天,欧阳白开着三菱吉谱,我们一起开赴汨罗八景乡,拜会韩少功老师。上次去韩老师家还是2006年7月底,一晃四年了。同行者也是欧阳兄,回来后的7月30日晚,我写了一首诗《和欧阳兄赴汨罗梓园》,收入诗集《穿着雨衣的拐角》中。这次去,我特意带上诗集,按《和欧阳兄赴汨罗梓园》一行行走完,就到了韩老师家。一进门,我将那首诗拿给韩老师看,他哈哈大笑,觉得很有味。
但毕竟四年未去,出乎意料的是,上到兰家洞水库大堤,竟迷了路。本来路走对了,我觉得没那么远,要欧阳白掉头,换一条路,结果上到山顶,得以俯瞰水库全景,真个是美不胜收。只是苦了欧阳白,在狭窄的山道上再次掉头,大秀了一把车技。
梓园更加林木葳蕤,浓阴匝地。韩老师半月前刚来,师母回长沙娘家了。我们杂七杂八聊着天,一片清凉。正好八景学校在筹备明天的中考,中餐便去学校吃,很是热闹。看见了老熟人兰老师,结识了新朋友郑叶新乡长——气质好、素质高的美女乡长,对全乡如数家珍。她在席间和我谈到对八景环境的保护,而不是急于开发,让我甚为激赏。乡镇和村一级干部素质提高了,中国农村或许会重现生机。
6月22日 阴 星期二
上周四,和欧阳白去汨罗韩少功老师家,白兄送了一本《诗屋2009年度诗选》给他,我那天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昨天,收到韩老师发来的邮件:
“读了你的诗,很喜欢。给儿子的最后那句,爸爸一冒出水面你就要把爸爸钓起来,又有趣又动人。欧阳白也是功不可没,诗集编得好。中宣部应该给他发奖杯才对。老韩。”
韩老师说的是白兄在书中选的一组拙作《给儿子的十五行诗》。诗屋年选越编水准越高,这次入选的安琪、解、李少君、雷平阳、李发模、洛夫、马永波、娜仁琪琪格、潘洗尘、欧阳白、秦巴子、郑玲、周瑟瑟等的诗歌都十分精彩。
欧阳白的序写得好,标题是《好诗主义与旗袍》。他说:“‘好诗主义’真的会流行起来吗?我可以不经思索,就直接给出答案,‘好诗主义’在任何一截时间段都不会流行,正于多年前一个流行的话题:‘旗袍会流行吗?’现在我们可以回答这个连续提出多年的问题,旗袍根本就不会流行,它注定只是少数人喜爱和重大庄重场合的盛装,其余人在其余时间还是喜欢穿休闲装。”
同样,收到《作品》第六期,扉页有熊育群的文章《离场者的背影》。他说:“关于自然的描写,也如水一样从文字的石缝间漏落。充满灵性与神性的自然,那是人类精神升华出诗意境界的地方,但我们正转过身来只面对人类自身甚至只是身体,我们正从这个世界的广大走向狭小。”
诗屋提倡“好诗主义”正是想让诗歌创作从狭小走向广阔,让诗歌呈现表达与审美的多种可能性。但现在看来,真正的好诗、好的文学作品也许永远是小众的,就像旗袍一样。
6月24日 雨 星期四
昨天上午,《晨报周刊》两位记者张云和李林冬来我办公室,他们要做一个有关“书信”的专题策划,问我一些有关书信的故事。我大约是十岁那年写的第一封书信,写给住在老家对面村庄的表姐,劝她不要和一个“小阿飞”谈恋爱。这个故事我写进了长篇散文或者短篇小说《疯子》中。表姐当然没有听我的,她和那个“小阿飞”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目前生活得很不错。
我的书信对象大约有三种人:一是文坛师友,一是读者,一是我资助上学的女孩。很多信我保存至今,通信最多的师友有涂静怡、戴海、左郁文、韩少功、薛忆沩、彭钢、于沙等。前晚翻检这些信件,竟然还发现我担任《大学时代》执行主编时,作家梁晓声给我的来信,推荐他学生的稿件,信写得十分恳切,可以想见其为人的厚道。
我留存的信件,除与台湾文友的手写通信持续至今外,其余一概到2003年打止。也就是说,从2003年开始,就主要使用电子邮件了。手写书信的时代很可能一去不复返。
以前没有报刊,更没有广电网络,传播基本上只有两种媒体:公告和私信。公告是大众传媒,贴在墙上及其他敞亮处;私信是小众传媒,大多在两人间往返。过去人们很看重信件,“家书抵万金”,手写书信负载着通信双方的海量信息,永为电子邮件所不及。
7月6日 阴雨 星期二
北京书友李黎明向我隆重推荐野夫的《尘世·挽歌》,新星出版社出版。我买来,一读辄陶醉其中。我说“陶醉”这个字对野夫和他的书可能有点残忍。野夫的千钧文字乃血汗铸就、性情陶冶而成,几乎是用命换来的,是用他家族中无数条人命换来的。这样的珠玑说是价值连城都不为过。2010年,我哪怕是仅仅只读过一本《尘世·挽歌》,都不算是没读书了。
据我的了解,这本书前些年一直无法在大陆出版,因为书中题材过于敏感,很多名社望之生畏。后来易名为《江上的母亲》在台湾付梓,并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野夫是获得这一奖项的第一位大陆作家。随即,该书又换了一个书名在香港出版;并很快得以在大陆问世。书亦如人,命途坎坷,但最终能脱颖而出,终归要感谢这个时代的进步,感谢这个时代政治的开明。
7月11日 晴 星期日
80后作家兼赛车手兼公共知识分子韩寒主编杂志,当然算得上一桩新闻。以韩寒的影响力,《独唱团》足可变成集结号,比南非世界杯的祖拉还吹得呜呜直响。这不,《独唱团》创刊号限量发行,据说湖南地区只能拿到一千本。而杂志封底条纹码上标注着:“湖南地区发行,定价16元。”在纯文学杂志中,这个价钱高居人上,似乎包含了韩寒飙涨的人气。
《独唱团》创刊号差强人意。一头一尾最好。头条,周云蓬的《绿皮火车》显示出与他唱歌作词相匹配的才华。尾声,韩寒自己的大作《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表明,这小子已经有资格和这个世界好生谈谈。不是谁都可以和这个世界谈的,那得有范儿。这范儿,韩寒有了。三十而立,他就立了这个。有的日进斗金,有的平步青云,有的东邪西毒,都未见得有这范儿。这范儿的标准是:一,长身玉立;二,特立独行;三,洞明世事;四,一呼百应。这四样,韩寒俱足。独唱成团,便不是怪事。
《独唱团》出来,我生怕看到的不是韩寒,是郭敬明。还好,看到一点郭敬明的影子,但擦亮眼睛,仔细一看,终究是韩寒。这里面很少有传统的知名作家,大多是年轻俊彦的集结,有两三位老者或准老者,如林少华、欧阳应霁、石康等,文章都不够好。年轻高手如咪蒙《好疼的金圣叹》、火蜥《幸福村》、罗永浩《秋菊男的故事》,让人惊艳。最年幼的王子乔,看照片不过一懵懂小鬼,他的大作不是惊艳,而是惊世骇俗,全文如下:“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和你了。但是纸币在飘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算钱。”
《独唱团》创刊号问世前,韩寒表态“郭敬明算年轻人的楷模”,向梨花派诗人致歉。为韩寒日渐成熟而欣慰的同时,不禁亦捏把汗:在中国社会,成熟往往不是好词。《独唱团》是不是个好词呢?我以为,暂时是个中性词。中性词未见得不好,它保持了多种可能性。
7月13日 阴 星期二
韩寒创办的《独唱团》杂志出了创刊号,复生托同事带了一本给我。《独唱团》由山西出版集团书海出版社出版,严格意义上说,是一本以书号代刊号的杂志,略显违规。但刊物处理也很巧妙,不叫“第一期”,而称“第一辑”,算是打了一个擦边球,得分。
《晨报周刊》第128期,复生做了一个有关《独唱团》的策划,《<独唱团>试用报告》,选发了拙作《<独唱团>是个中性词》,另有何立伟、谢宗玉、邹容、守备三师等的高见。
江冬送来他编辑的《发现阅读·欢乐课堂》初中生卷。邓湘子主编,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封面是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名言:“一个人只有在他懂得爱的时候,才会成为真正的人。”该书选登了我的一篇文章《最好的奖励》,文后出了四道题,认真看了下,我也不一定能答好,还是让聪明的孩子们去答吧。
7月20日 晴 星期二
毛泽东文学院“谭谈工作室”纪红建先生来函,作家谭谈牵头组织作家、画家、摄影家对湖南现当代著名艺术家的故居进行考察,通过著文、摄影、绘画,反映这些文化名人故居的现状。这的确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谭谈先生邀请20位湖南诗人为20位湖南籍现当代文化名人每人创作一首诗歌,再请20位书法家将这些诗歌变成书法作品,会同考察成果,于今年12月,在毛泽东文学院举办一次展览。交给我的任务是,为《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写一首诗。我想,就为杨沫女士写一首十五行诗吧。
在网上翻阅杨沫的资料,看到张中行先生年轻时写给杨沫的一首爱情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
多感人的诗篇!诗中的“杨花”即指杨沫,但后来两位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可见,爱情与爱情诗也是不太搭界的。有好的爱情诗未见得有好的爱情,但我以为,即便没有好的爱情,有好的爱情诗也是好的;正好比,即便没有好的爱情诗,有好的爱情也是好的。杨沫啊,杨沫,我可再写不出如张中行那般的“杨花诗”来了。
7月26日 晴 星期一
晚上6点,罗鹿鸣有请,到锦绣红楼817参加“诗人聚会”。参加聚会的诗人有:唐朝晖、聂茂、龚道国、刘起伦、李杰波、谢午恒、龚湘海以及昕孺。
鹿鸣兄到常德当行长后,把常德的诗歌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对于常德诗歌的意义,堪比欧阳白对于郴州诗歌的意义,都是在一个比较沉寂的地方,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
道国,我还没读过他的诗,但他的散文越写越有心得,最近他升迁了,我们举杯祝贺,他腼腆得一脸彤红。我看好这种人的出息。
我第一次见到聂茂夫人,苗条静淑,很知性。倒是聂茂的肚子大了。茂兄写诗、作文、治学、办报,格局越来越大,肚子大也许只是格局大的反映之一。
杰波一见到我,就说他现在专攻理论了。我说好啊,现在正缺理论家。他略显郁闷地说,他攻的是新闻理论。然后,轻轻摇了几下里面长着一个瘤子、外面披着一头长发的脑袋。
起伦在国防科大,贵为“大校”,他最怕我们喊他“将军”。但诗人都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将军长将军短的,弄得他云里雾里。几杯酒下肚,拍着桌子喊服务员,要她把老板叫来,赶快拿照相机拍下这“红楼十余贤”的靓丽身影,挂在大堂中央,为酒楼增色。吓得服务员落荒而逃,好久不敢进来倒酒。鹿鸣是摄影专家,他说,老板不拍,我们自拍。举起形似迫击炮的一个大玩意,对着我们一顿猛按。起伦煞有介事地接过去,左瞧右瞧,认真质问摄影师:里面有胶卷没?
席间,得到聂茂主编的《三湘人物周刊》,办得挺大气,里面关于彭崇谷、冯明德、郭辉、吴茂盛、王又元的报道,我都喜欢,特别是王又元的画,大雅大俗,十分耐看。如果要挑点毛病,官员作家稍嫌多了些。有趣的是,某先生的简历中有“现任XX市环保局副局长兼党组副书记(正处级)”字样。他自称为“朴实而可笑的幻想主义者”,我看,朴实虽未见,可笑则有之。这位幻想主义者,会不会还对“副厅”抱有幻想呢?
我想冒昧对官员作家们提一个建议。从政与作文、治学毫不矛盾,官员文学家也是中国官坛与文坛的传统,虽说未见得优良,但也不一定低劣。当代中国,有不少官员的文学作品毫不亚于某些职业作家。但我建议,官员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中,简历最好不要提到自己的行政官阶(有关文艺的民间团体任职除外)。我看到,有很多优秀的官员作家就是这样做的,恕不一一表扬。
8月3日 晴 星期二
余三定老师,文学评论家,学者.我的第一本诗集《月下看你》,就是余老师作的序,那时我们还没见过面,是好友许奔流牵的线。我创办《大学时代》杂志,余老师和诗友刘创给予了不遗余力的支持,至今让我铭感五内.我曾写过一篇《儒师余三定》的小文章,刊发于《大学时代》2006年第6期,推重老师的治学与为人。
7月30日,余老师在《人民日报》发表《岂能“只认衣裳不认人”——“CSSCI风波”引发的思考》一文,直指中国学术评价体系的弊端,“一 些论文评价机构和评价者也不看论文质量如何,甚至完全不阅读论文,只在评基地、评项目、评职称时核对一下该论文是否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上。这就造成了学术评价和学术活动中‘只认衣裳不认人’的弊端,即原本作为一种手段的学术评价机制反而成为学术研究的目的。从长远来看,过度抬高这种学术评价机制,有悖于学术研究的原初目的和终极追求,会消解学术研究的崇高性和严肃性。”
读过该文后,我给余老师发了一条短信:“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问题太多,已缺乏公信力,应该有专家站出来说话。老师发言体现学者良知,弟子敬佩不已。”
8月9日 晴 星期一
童银舫先生寄来他主编的《上林》杂志第3期,这是办在浙江慈溪市的一本读书民刊。说“民”,也只是没正式刊号而已,看其主办单位乃市委宣传部等,“民”的后面仍然有官撑台。慈溪市是余秋雨的老家,这期杂志“余味”较浓,有关于余秋雨的新闻,有对他的访谈,还有评论余秋雨作品的文字。既要官方支持,又重名人效应,这对于一本读书类民刊的生存与发展,还是必要的。《上林》的很多作者都是老朋友,如陈学勇、眉睫、黄岳年、林伟光、袁滨等,读刊即如老友聚会,其乐何如!扉页自牧的书法“静水流深”,抵得上一篇美文。
难得的是,从本刊中看到一个久违的老朋友——乔延凤老师,前《诗歌报》月刊的主编。我办《湖南教育报》时,先生鼎力支持,多次赐稿,至今感念。他写的这篇《书香最怡人》,便提到曾发表在《湖南教育报》副刊的《我的启蒙教育从识字始》,正是我的责任编辑。先生在文中说,发表在《湖南教育》,应有误。在此,向乔延凤老师遥相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