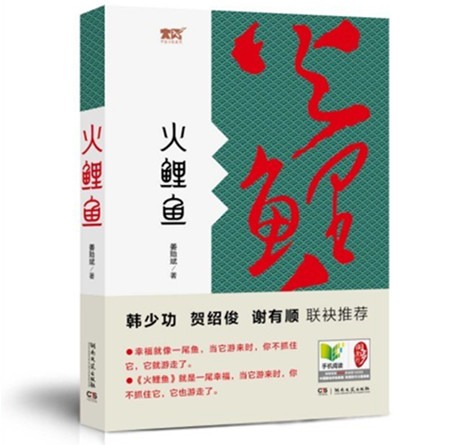
火鲤鱼(长篇小说)
作者丨姜贻斌
大 暑
日头落山石山阴,罗汉伸手扯观音。
神仙也要耍风流,山中百鸟也思春,
难怪凡间世上人。
——山歌
一
车把和王淑芳本来是应该走出去的,走得越远越好,像水仙银仙和雪妹子那样走得远远的,他俩终于没有走出去,从县城又回到渔鼓庙。
渔鼓庙已不像以前是一片茂盛的菜地,也没有菜地色彩斑斓的花朵,吐红滴翠的菜地已经改头换面,种上了水稻。那正是水稻扬花的季节,细碎的白花,像无数小小的蝴蝶振翅飞舞,似乎把强烈的阳光也振动了。应当说,这算是乡村赏心悦目的风景,而车把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对家乡作物环境的突变产生的空落心境呢?还是对重返家乡的无奈和叹息?
毫无疑问,车把又见到王淑芳的丈夫。
多年前,那个窝囊的男人重新出现在他眼里。他不想见到这个人,而生活就是这样,有些人并不是你不想见就见不到的,他总会在你的生活中出现,像一个可憎的影子。
那是一个长相委琐的男人,黑色的脸皮,邋遢,阴着脸,眼神中好像对世界充满仇恨和敌意。车把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老八,谁知这个家伙越长越缩,像一只风干的萝卜。
那是7月下旬的一天,天气很热,阳光火一般地照着,车把坐在茶馆门口,无聊地看着马路上的行人,还有飞腾的黑色灰尘。车把时而朝雷公山看一眼,好像才发现它已经变了,再不像以前丰满。现在,它光秃秃的,泥沙大量流失,黄色的砂石裸露,密集的松树都到哪里去了呢?好像眨眼间,它就从苍翠的山岭变成苍凉的山地。他想起儿时跟着伙伴们在山上追打的乐趣,以及篮子里盛满着喜悦的收获,不禁有淡淡的惆怅。
这时,马路上出现了老八。
老八从茶馆前面走过,车把心里不由一震,目光死死地盯着他,以为老八会重新挑起熄灭多年的战火,所以,也暗暗地做了准备。
老八低头慢慢地走着,看架势好像不是来吵架的,大约是路过吧。他没有望茶馆,自然也没有看见车把。他似乎不晓得车把带着他的女人回来了。他背有点驼,生活的重担似乎都堆积在上面。好像还咳嗽,咳得很空洞,一点痰也没有。
咳嗽如果没有痰并不是好事,属于燥咳。车把想,如果老八过来打个招呼,他可能会出于同情,告诉他几个治燥咳的方子。车把很聪明,懂得很多药方子,在长沙的餐馆做药膳时,看过不少药书。
他看着老八远去的背影,居然有点失望。这个人难道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吗?难道不晓得他们回来了吗?渔鼓庙才有多大?即使是耳屎大的事情,也用不着一根烟的工夫,人们就会晓得。
如果老八来吵架,说不定车把会兴奋的,当然,他不会动手打他。他要当众嘲笑他,羞辱他,让他再次出丑。而他却默默地走掉了,也没有看他一眼,车把好像失去一次胜利的机会,随之,又产生出对这个男人的同情。
这是一个可怜的家伙。
茶馆的生意容易料理,所以,车把也没有请帮手。楼下喝茶打牌,楼上有五个小姐,那都是邻县的。车把给茶馆取了个店名,叫好再来茶馆。茶馆谈不上装修,也无须装修,像这样的鸡毛店子,如果装修就划不来。再说,又不是县城,那是要有些讲究的,这里讲究什么呢?无非是买几张桌椅和床铺。车把对于店名很得意,它包含了两层意思。
有个打牌的老者问车把,你为什么不给店子贴副对联?
车把说,我想不好。
老者笑了笑说,我倒是替你想了,不知可不可以?
车把说,那你说来听听。
老者说,上联是:接五湖四海客;下联是:送三教九流人。
在场的牌客大笑,都说,好好。
车把说,对子倒是好对子,只是我不会贴。
老者幽默地说,我白送你一副对联你都不要,哪天我到县城送给店铺,人家是要打发红包的。
车把承认说,那有可能。
那天,车把一直坐在门口,望着尘土飞扬的马路,希望那个男人返回来。他要观察老八到底看不看茶馆一眼,或者说,看不看他车把一眼。
这时,王淑芳从屋里出来,问他为什么老坐在这里,他没有说看到老八,搪塞地说,反正没有什么事。他不想对她说起老八。
从早上开始,茶馆就有人来打牌搓麻将,所以,楼下闹哄哄的。这时候,楼上安静得要命,几个疲倦的小姐还在梦乡,她们要睡到中午时分才起来,然后,陆续接客。
直到下午,老八才出现在茶馆前面的马路上,车把好像是专门研究老八的,所以,也一直坐在门口,很有兴趣地看着他。心想,这个家伙又出现了。令他惊讶的是,老八竟然朝茶馆走来,好像他是这里的常客。
这时,王淑芳也坐在门口跟车把说话,对于老八的出现,两人显然有点措手不及,不知说什么才好。当然,只有那么一瞬,车把冷静地站起来,警惕地把女人挡在身后,担心老八突然拿出凶器或爆炸物,这不能不防——他心里积累了多年的仇恨。
老八一步步走近,然后,不屑地站在门口,像不认识他俩样的,也好像完全不记得以前的痛苦,漠然地说,给我来一个。
车把两人这才恍然,明白他是来做生意的,不由暗暗地松口气。生意来了不能不做,不管他是什么人。当然,车把两人还是有点尴尬的,虽然希望茶馆有生意,而这毕竟是老八。
车把两人没有跟他说话。车把看女人一眼,示意她走开,然后,带着老八上楼,把老八带进一间屋里,屋里充满浑浊之气,那是汗气香气潮气的混合气味。
然后,车把叫五个打扮粗俗的小姐进来,手一扬,让他挑选。小姐们做出挑逗的动作,把发亮的眼神死命地在老八身上舔,效果居然很好。老八冷漠的眼睛顿时贼亮起来,朝小姐们脸上胸上一个个扫,扫一阵,最终点中那个叫小艳的妹子。
车把走下楼,对王淑芳悄悄说,这个家伙也晓得开洋荤了。
王淑芳没有说话,好像没有听见,也好像在想什么心思,脸上流露出微妙而复杂的神色。她低着头在给炉子加煤,然后,把烧完的煤球灰倒出去。
车把却在猜测王淑芳的心理,她看见老八来睡小姐不知是什么想法。愤怒?还是嫉妒?还是无事一样呢?猜来猜去,猜不出来,也不去猜了。他想,只要老八不是来吵架的,来做生意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说实话,还应该感谢他来捧场,老子只要有钱进账,管他是老八还是老七老六。当然,如果替老八想想,他能够来这里还真不容易,他首先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这里有他仇恨的情敌和女人。
车把还想起一句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老八轻松地下楼,黑色的脸上居然有了光彩。他面无表情地把台费丢在桌子上。车把拿出烟递上一根,老八像没有看见,抬脚往屋外走去。恰巧碰到王淑芳挑水进来,王淑芳连忙让了让,老八也没有说话,走了。
白天,车把两人没有为这事议论过,也不太方便,有客人们在。其实,客人们也看到老八,都没有议论,彼此间心照不宣。王淑芳的脸上却再没有笑容,心里肯定是不高兴的。
一直到睡觉时,王淑芳终于憋不住,对车把说,我不喜欢在这里看见他。
车把故意说,哪个?
还有哪个?你难道不明白吗?王淑芳不高兴地说。
车把叹口气,说,我们是做生意的,管他是谁,只要能来,都欢迎。
我不喜欢在这里看见他。王淑芳气愤地叫起来。
车把不愿意在半夜吵闹,嬉笑着说,你这个人也真是的,他又不是来戳你那个东西,他戳的是小姐,你生什么气呢?淑芳,我们只要有钱进,管他什么人,我们一律欢迎,只有这样生意才做得起来。
王淑芳心里还是不平衡,说,少他一个,我们难道就会饿死?
饿死当然是不会的,车把说,做生意最要紧的是人气,人气旺,钱收不赢。少个人,会少一份人气,多个人,会多一份人气。你不喜欢看见他,你回避就是。
王淑芳冷冷地哼一声,不再说话。
二
当然,从心理上说,车把也不喜欢老八来睡小姐,也不愿意看见老八。问题是,这一带唯有车把这里有小姐,老八不来这里又去哪里?再者,这里很方便,脚一抬就到了,难道叫他去水井头?叫他去县城?
不管怎么说,老八开始频繁地出入茶馆。从某种角度说,就是有意无意地侵入车把的家,这多少对他这个家是个恶意的伤害,或是一个莫大的嘲笑。意思是明白不过的,嘿嘿,你们又拿老子怎么样呢?你们有本事敢把老子赶出去吗?你们难道不想做生意吗?老子有钱,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来,老子是上帝。老八心里肯定是这样想的。他还会想,我那个又老又臭的女人,就让你车把睡吧,老子已经睡厌了。现在,老子要睡白嫩的小姐,比你车把舒服到天上。
后来,车把有点不能容忍。那个家伙大摇大摆目中无人,虽然衣着很陈旧,神态上竟然有很大的不同,抬起骄傲的脑壳,眼睛望天上,好像他的钱放在天上,好像根本没有把车把两人放在眼里,好像是对他们无言的报复。多年来的仇恨痛苦和委屈,终于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得到尽情的发泄。
车把还注意到,老八每星期居然来两次,虽说花费没有县城贵,也不是很便宜的。那么,他一个死农民,一不做生意,二不打工,一年到头只围着田土转来转去,又有几个钱呢?他凭什么这样有钱?偷的?抢的?还是捡的?或是赌博赢来的?如果是赌博,他好像从来不在这里打牌搓麻将,那么,在哪里赌呢?总之,钱应该有个来路。而老八竟然像县城人很具有消费意识,每星期居然来两次。
想到这里,车把很不舒服,像毛毛虫在胸膛里爬来爬去,令他恶心呕吐。他想,老子和王淑芳在县城做过多年生意,现在又逼得我回渔鼓庙,每天辛辛苦苦,酸甜苦辣,也没有多少存款。这个家伙倒是潇洒,每个星期来戳两回小姐。
有一天,一场争吵终于爆发。
老八又来了,嘴里叼着烟,王淑芳看见他来,照例从后门走出去,以免尴尬。车把照例把他带到楼上点小姐。老八背着双手,把烟屁股丢到地上,脚一踩,然后,要一个小姐。
车把站在门外,呆了一阵子,忽然发现老八睡小姐很有规律性。他不像有的人喜欢叫熟悉的某个小姐,即使某个小姐已经出台,也要耐心等待。老八绝然不同,竟然轮流睡那些小姐,轮过一遍,又从头开始。他晓得在有限的小姐中吃着无限的新鲜。老八自从来茶馆,车把还没有跟他说过话,真的不想跟他说话,车把的心情也很复杂。
车把看他把小姐带进屋里,就下楼来。
没过多久,听见楼上发生激烈的争吵。
车把赶紧上楼,叫开门,那个叫色色的小姐精光地躺在床铺上,盖着被单大哭,泪流满面。老八穿着短裤,满脸气愤,也不顾车把进来,仍然大骂,骂得十分难听。
车把平和地问,哎,怎么搞的?
老八不接车把的话,也不看他,把脸愤愤地别到一边。
车把问色色。
色色伤心地抹着眼泪,说,他只给四十块钱,我说还少十块,他说下次给,我说小费没有欠账的,他就……打我……呜呜……色色抬起红红的手臂。
车把浑身冒火,对老八说,小姐说得不错,小费是不欠账的。说罢,又突然冷静,把火气死命地往下压,赶走一个客人等于少一份收入。车把说,这样吧,小姐的十块钱我先垫着,你下次来给我好不?
谁知老八说,鬼叫你垫?老子还少这几个钱?又赖皮地说,我来了这么多次,也给我打个折吧?
车把一听,忍无可忍,怒火又呼呼地燃烧起来,放在口袋里的右手握成拳头,发出格格的响声。最终,还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那好吧,这十块钱就算打折。
老八冷漠地笑笑,穿好衣服,望着小姐哼一声,噔噔地下楼。
车把拿十块钱给色色,劝道,别哭,跟这种人不要计较。
然后,心里很乱的车把下楼来,坐在门口呼呼地出粗气,烟抽得滋滋响,像灭火器,借此来平息内心的怒火。他望着老八的背影,觉得那一粒黑色的背影十分嚣张,似乎在嘲笑他。他恨不得追上去,饱以老拳。
楼下打牌的人大约过于专注,好像没有听见楼上的叫骂声,仍然发出吆喝声遗憾声和争吵声。这一切,车把似乎没有听到,在想着老八。娘的脚,依他过去的脾气,会把老八打一餐,打他个七窍来血。
想起在县城时,他饱受那个老家伙的窝囊气,男人的面子一点也没有了,不料来到自己的家门口,还要受这个家伙的气。车把很恼怒,又不想吵闹,那样会影响生意。他之所以叫王淑芳回来,是想仗着在自家地盘上,生意或许好做一些,不然的话,哪里愿意回来呢?唉,如今做生意真是太难,你要具备罕见的小心和无限的忍耐性,脸上必须时常保持职业性的微笑,像电视里的那个女人一样。
他曾经想暗地里把老八饱打一餐,让他哑巴吃亏做不得声,又担心闹出人命来。想起在县城,那个老家伙睡了自己的女人,若不是自己的忍耐性,恐怕也会闹出人命案子。看来在这个世上,只有忍辱负重才能够活下去。
车把想到这里,惊异自己的脾气有了惊人的变化,以前哪会吞下这口气呢?以前老八不是也来吵闹么?当时,许多人叫老八不要这样,可以坐下来谈。老八却大骂,你娘的脚,明明是我婆娘被他车把勾引了,还有什么好谈的?你们婆娘如果被别人睡了,还有心思谈吗?
当时,车把闯入灶屋拿起斧头冲出来,准备斫掉老八的狗脑壳。老八吓得飞快地溜走,再没有来闹过了。
现在呢,车把却一忍二忍三忍,他倒是希望能够这样忍下去,不再意气用事,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大。
他明白,今天等于是贴钱给老八嫖娼。如果是别人真的没有什么,算是请客吧。而且,老八还打小姐,这不是等于打他车把吗?以前客人跟小姐也发生过吵闹,劝劝也就过去了。而他是谁?他毕竟还是王淑芳以前的男人,那么,他车把等于在老八面前矮了一截,也许,这会成为老八吹牛的资本。所以,下次老八来,是不是问他要回那点钱呢?又怎能开口?明明是你自己说的打折。
车把又想,唉,矮就矮一截吧。古人也说过,忍得一时之气,省得百日之忧。再说,你车把从他手里把婆娘都夺走了,又如何解释呢?
那天,王淑芳买菜去了,回来才听说这件事,问,听说那个人在这里吵?
车把说,小事一桩,不要大惊小怪。做生意,哪里没有一点吵闹呢?
他没有把真相说出来,有点难以开口,王淑芳也没有问小姐,所以,事情也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