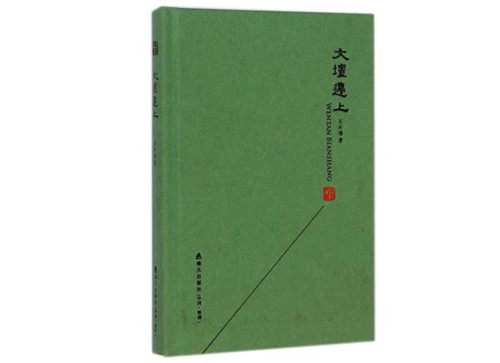
文坛边上·2009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7月12日 晴 星期日
网上得知,季羡林老先生于近日去世,大多报道称“最后一位大师的离世”。活到近百岁,离世没什么稀奇。身体好除了先天体质,还要性情平和;性情平和除了先天脾气,关乎心态涵养。所以活到百岁,生命本身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百岁老人都是生态上的“大师级人物”。至于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我个人认为,钱钟书之后,中国就没有国学大师了。大师不仅仅是某一学科领域的翘楚,而是应对整个社会文化、学术思潮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季老只是属于那个时代优秀人物的年长者。
季老走好!
7月17日 晴 星期五
《文学界》第7期“作家专辑”推出了凸凹、朱鸿与熊育群三人。朱鸿我不认识,凸凹是故人,育群是老兄,自然倍感亲切。八、九年前,我在《创作》做特约编辑,凸凹是我的重点作者,他当时好像在北京房山区某镇当镇长,小说以农村题材为主,写得大刀阔斧。我们有过一些通信,颇谈得来。因做《大学时代》杂志,没精力再为《创作》服务,与凸凹也没再联系了,惭愧的是后来也没读过他什么文章。
育群兄去广东前,在湖南的一家行业报纸办副刊,我们是同行,每年至少要在一起开一两次会,评评奖什么的。他很豪爽,喜欢大笑,加上个子高,笑起来特有感染力。去广东后,他写散文出了名,却不忘记小兄弟,在《羊城晚报》办副刊时经常督促我投稿,可惜我生性懒惰,只投过一次,他发在“花地”上将标题改为《时间不在花瓣上跳舞》,不久被《杂文选刊》转载。等第二次再投稿时,他做广东文学院院长去了,但仍然将拙作推荐到《粤海散文》杂志。其深情高义,由此可见一斑。
7月29日 雨 星期三
收到台北《秋水》诗刊第142期。照例在封面与扉页之间,夹着该刊主编涂静怡女士的一封小笺,斜斜的字体,清秀雅致。平时的信件都是问好、询问近况、回忆交往的美好往事,这封却有着别一种况味:
“昕孺:你好。没有时间回信,是时间不够用。晚年多病,花在去医院等看病的时间多了,今夏牙痛,拔了三颗牙,治疗就得花三个月,十分无奈。你写向明的诗,刊在第1期的《秋水》上。现在用航空给你寄上,请慢慢欣赏。谢谢你长久以来对《秋水》的爱护,那也是一种缘分。剩下18期了,我决定160期让《秋水》划上完美的句点。够久了,一本民办诗刊维持了四十年,是不容易的事。谢谢你陪伴我们走过许多的季节。一千个祝福。涂静怡,2009.7.21”
这样的文字让人伤感,这三十多年来,静怡女士历尽艰辛,也乐在其中,她与《秋水》人刊合一,在中国诗歌史上几乎无人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传奇的女性。我与《秋水》有近二十年的缘分,包括2004年能去台湾,都多亏了《秋水》的盛情邀请,对静怡女士和《秋水》,我是怀着一份别样的感戴。但在三年前,我就写信劝静怡女士停办《秋水》,以身体为重,因为办一份如此精美的诗刊,要花费精力、付出心血实在太多了。今天我终于看到了《秋水》的倒计时,心里有一丝安慰,但18期还有4年多时间,依然很不容易。一本民刊办了四十年,从未中断过,这是一项如何浩大的工程,这是一种如何执著的信念呢!
8月15日 晴 星期六
话说11日,我还在山东新泰,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但热不过阿滢、石灵和万志远等新泰朋友们的热情,继前一天我们去新甫山看了“新甫之柏”,这一天又前往天宝镇徂徕山欣赏“徂徕之松”,尤其重点去了李白曾和当地五位名士一起喝酒、吟诗的“六逸堂”,更是兴会无前,也多少补偿了没去济宁太白楼之憾。阿滢、石灵、袁滨、广袖、我,加上带队兼导游的天宝镇人大主任孟磊,此君曾习小说,对齐鲁文化颇有研究,我们正好一共六人,拍照留念,戏说组成新的“六逸”。
下午三点,广袖的车把我送到新泰汽车站,和袁滨、阿滢、广袖、石灵四位仁兄拥抱作别,前往此次山东之行的最后一站济南。五点四十分到济南,因是下班高峰期,怕堵车,故乘三轮车至省委机关医院门口,自牧在三楼办公室等我,一直未曾见过面的老朋友徐明祥也在。自牧兄不仅帮我买好回程车票,预订了宾馆房间,还送给我他著的《存素集》《四面集》等书籍多种,以及去年第六届民间读书年会的纪念品:用泰山石制成的笔筒。明祥送给我他的大著《潜庐藏书纪事》《潜庐诗草》两种。
晚上,自牧在佛慧山一餐馆为我接风洗尘。饭后,去读书界声名赫赫的“淡庐”参观。自牧的新居在佛慧山谷,风景极好,再坐拥书城,真是拥有福慧无数!
8月27日 晴 星期四
这向一直在写《齐鲁散记》,就像去年写西藏一样,人在长沙,心在胶州。《齐鲁散记》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十城记”,第二部分是“七友记”。
阿滢将我写的那篇《秋水文章不染尘》发到博客上后,《天津日报》社罗文华先生在后面留言:“读罢此文方想起来,这个吴昕孺原来就是吴新宇啊。他是我二十年前的朋友。他为什么要改名?蓝苹改江青,是革命需要,吴兄为了啥?”文华先生确系旧友,应该是十多年前,成都龚明德先生介绍我们认识。那时,明德先生介绍我与不少优秀的读书人联系,如董宁文、张阿泉、罗文华等,感谢他的厚德。但搞《大学时代》几年,每天应酬俗务,荒废文事,读书界的朋友们都很少联系了。所以,我借阿滢兄的地盘给文华先生留言:
“问好文华兄,愚弟确是新宇,并未如蓝苹那样改名,只不过取一个笔名而已,官方资料上仍是‘新宇’。只是觉得人生如寄,文字如戏,换个名字做个隐者,好玩罢了。因为2002至2006年做了多年书商,宛如伧夫俗客,与一切清雅文友均无联系,如今重新读点书,写点文字,还盼文华兄玉正。昕孺敬上。”
8月31日 雨 星期一
昨天,复生来电话,说历史学家雷颐来长沙讲课,晚上在白沙源餐厅荷源包厢有个小型聚会,问我有没有时间参加。我正好想出去透透气,这么好的学习机会,怎能放过!聚会的除了客人雷颐教授,还有朱正老师、孟泽教授、复生,以及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制片人柳理和他的部下余学用、李芳。
雷颐教授籍贯长沙,他的长沙话讲得很流利。这次来长沙是参加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的国庆专题录制工作。雷颐认为,改革开放30来中国最大的变化是有了公共空间。但许多陈旧的东西根深蒂固,要消除它们并不容易。他说,他一位同学从美国回来,参观潘石屹打造的现代城,在一栋楼前拍照,遭到保安强行阻拦,说“这是我们潘总的房子”。这位同学据理力争,他很不理解,因为他没有去潘总的内室拍照,他是在大街上,是在公共空间拍照,为何要遭到这样的无理阻拦呢?更奇怪的是,同行的朋友们都劝他算了,而不是一起指责保安,争取自己在公共空间的权益。
朱正老师在思想界、读书界名头很大。抱歉的是,和这样的泰斗同居一城,我却是第一次见到老先生。老先生头发银白,思维敏捷,谈锋甚健。他25岁那年就出版了《鲁迅传》,50岁的时候,《鲁迅传》出第二版,75岁的时候《鲁迅传》出第三版,每25年一个台阶。
既然是聚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很是有味,但以朱老先生和雷教授为主讲。我们讨论了鲁迅与周作人交恶的具体原因,讨论了三年自然灾害中国死亡人数的具体数字,讨论了右派和左派名称所隐含的悖论。
朱老师说,他和钟叔河被划为右派后都进了劳改农场,他被判三年,钟老先生更长,判了十年。平反后,他落户湖南人民出版社,他最为得意的事件是责编了李锐的著作《庐山会议纪实》;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骆驼丛书”也是他的策划和责编。他担任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期间,首次在国内推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我手头就有这一个版本,那是1987年我读大二时,通过同学关系买到的。朱老师说,当时武汉市新华书店没有征订这本书,听说这本书卖得很好,就到长沙来要求进些书。那时书刊发行远没有现在这样市场化,出版社发行科以没有征订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一气之下,告到宣传部,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是淫秽书籍。朱老师因此而丢掉总编辑职务,与胡耀邦丢掉总书记职务几乎同时,并被记行政大过一次,直到现在他还背着这个“大过”。
聊到十点,散场。正好与柳理同路,他把我送到水木轩。柳理是我的老乡,师大的学弟,曾在长沙县六中当过三年教师,后到教育电视台工作,早已是台柱级人物。我读过他的古体诗,写得很棒,今日一见,洵洵儒雅,才子也!
9月5日 晴 星期六
昨天下午,刘怀彧带着西藏诗人陈跃军从西而东,跨越湘江,到留芳宾馆。我在麓山厅为跃军接风洗尘。怀彧兄,即是我前面介绍过的写《朋友三四》的那位书生,正巧他在组织部供职,可以关照下跃军。
高兴的是,欧阳白、远人、龚军辉、李婷婷等长沙诗人代表也大驾光临,喝的是润帝酒,饮的是长沙水,吃的是湘菜,电视里看的是“快乐女生”,湖湘文化无处不在。
9月25日 阴 星期五
陕西文友胡树勇寄来散文集《守一不惑》,“紫槐香散文丛书”中的一本。树勇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中很有建树,同时又在文学创作中勇于开拓,且成绩不俗。书中有一篇文章引起我的关注:《被以讹传讹的作家崔八娃》。文章写到周铁钧先生的散文《崔八娃逸事》讹误频频,却被《文汇报》《语文报》等一再刊传。树勇曾和崔八娃一起参加过安康市作协的代表大会,对崔八娃的了解应比周先生更多,也更准确。希望媒体重视树勇的这篇文章,以澄清讹误,让八娃老人九泉之下安息。
10月5日 晴 星期一
昨天中午,请海南文友赵瑜和周建国到兴汉食府吃饭,宗玉、跃军、文培也来了。赵瑜和宗玉是老朋友,我们则是第一次见,感觉他比照片上稍瘦。
下午,宗玉开车一起去岳麓书院和爱晚亭,在半山亭笑谈半日。返回到杜甫食府晚餐后,宗玉送赵瑜和建国去车站,他们前往吉首;我和跃军一起沿湘江风光带溜达,到兴汉门坐各自要乘的公交车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