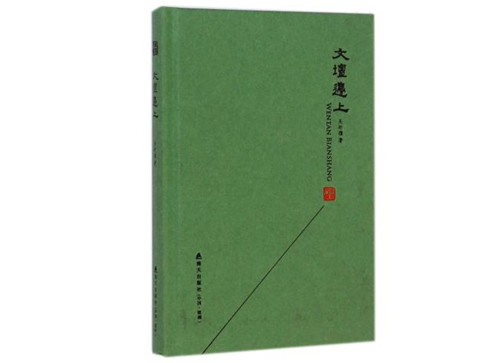
作者丨吴昕孺
9月23日 晴 星期二
昨晚,晓梦斜阳请韦白、杰波两口子和我在四方坪的新东方酒楼聚餐。那一带我应当是很熟悉的,在金帆小区住了五年,但找这个新东方酒楼竟然颇花了一番功夫。大家照例以诗歌为主题夹叙夹议,杰波看重诗歌的“主题”,而韦白认为应“技巧先行”。杰波是对比较成熟的诗人说的,韦白则是针对广大诗歌爱好者和写作者,所以,他们的道理都对。我也谈到如何去理解诗歌,以我个人的经验,“诵”是一种最好的方式。有的诗歌应朗诵,比如浪漫主义作品,宜于广庭大众之中进行朗诵;有的诗歌应吟颂,比如现代主义作品,宜在灯下、林间独自吟颂。只有通过出声的方式,诗歌对内心的浸染和对灵魂的震撼才能产生最大的效应。晓梦斜阳谈到她看到西川的一句诗“把羊群赶进大海”,看和读的感觉完全是两回事。
年过八旬的老诗人于沙寄来大著《诗路花雨》,集中了一些诗人、评论家和读者对他历来作品的评论。于老师对我曾有知遇之恩。1988年,他主编《湖南新时期十年优秀文学作品选•诗歌卷》,破例选了我这个在校大学生的作品两首,很多成名诗人都只上了一首。后来,广州《华夏诗报》要在头版刊发写他的一个特稿,他把这个光荣任务慷慨地交给了我,我那时还很少写诗以外的文字。文章写成后,到于老师家里请他修改,我至今记得他提醒我写文章要注意的一点:“‘就’字不要用得太多。”这样的指点让我受益终生。
10月3日 晴 星期五
长假是让人感到自由和幸福的。我一般不会选择长假出远门,因为我怕人山人海。让别人出行去吧,我留在家里读书。前面两天的主题是读书和写作,读帕慕克的《新人生》,读里尔克诗选。
写作主要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几个朋友野心不小,要做湖南最高端的白酒,取名“润帝”,据说要卖到一千多元一瓶,嘱我写一篇《润帝赋》,拟个广告词,将湖湘文化、帝王文化、山水文化与酒文化联系起来。平时写篇文章并不难,但要写为市场营销助力的文章难度还是很大的。第二个任务是为下个月的师大读书讲座拟一个提纲和初稿,写起来也不容易,因为读书要谈出新东西来很难,还要兼顾趣味性就更难了。不过,我以前对自己读书没做过总结,这回算是梳理了一下。
10月5日 阴 星期日
我一直在想,改革开放30周年,这样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会有哪一本思想性杂志来出一期专刊,主题就是对这30年进行总结与反思。而第一主题应该是反思,这不仅能体现中国思想精英的在场意识与使命感,对政府也是一个很好的监督与促动。但至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这样一本杂志。中国本来就没几本思想杂志,但我不相信中国没有思想者,所以杂志的萎靡在于其自身,不能完全怪读者。《半月谈》、《今日中国》、《传播与社会学刊》做了专刊,主题仅仅是总结,凡以总结为主的专刊信息量都不会很大,容易做,又不担风险。中国期刊大多采取这一方式,主题先行,思想滞后,或者根本就没有思想。
《读书》不愧是中国读书界第一刊,第10期的几篇文章很有分量。像马国川对吴敬琏的专访,像周其仁的《改革三十年感言》和陈彩虹的《世界大转折的伟大预言》都有真知灼见。这三篇文章放在一起是有内在联系的。这种内在联系要倒过来看。先看陈彩虹的《世界大转折的伟大预言》,在大家看来,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元更是成为国际货币,但美国人的做法最违背经济规律,美元不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和物质财富的基础上,而是在玩所谓“制度创新”和“金融产品创新”的货币魔术,用这种魔术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也积累了巨大的债务。这种债务使得美元几乎变成一张张纯粹的“欠条”。当全世界都拿着美元这张欠条向美国索要产品和服务的时候,美国已根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金融和经济危机便一触即发,美元崩溃,并引发政治和社会危局。陈彩虹的文章认为,崇尚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创造财富的国度将主未来之沉浮,因此,世界即将实现大转折,取代美国的新大国呼之欲出。是谁将取代美国呢?文章没有点明,但看行文的语气,似乎中国很乐观,至少也该是候选国之一。
中国真的能成为新的“地球之王”吗?往上看,是周其仁的文章和对吴敬链的专访。周文简洁明快,写得好,但与吴的思想十分接近,故不说。我们来看吴敬链的专访。吴敬链在专访中始终贯穿了一个字:“忧”。看美国笑话的人可能认为中国这回该出头了,其实,中国的问题并不比美国少,也不比美国小。吴敬链认为,改革开放30年是一道坎,中国还在过改革开放的大关,这一关如果跨不过,不要说在地球上称王,就是自己内部的事情都会焦头烂额。
那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呢?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改革开放有偏离当初制订的方向的危险,它可能无法带来全民的共同富裕,而始终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先富之后更富;穷人虽然看上去比以前富了一点点,但与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比,已经相差不可以道理计。穷富本有命,这个还不至于影响心态,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富人的致富之路正是沿用美国人的“空手道”,而美国人使出的是经济上的空手道,中国富人使出的却是权力上的空手道。也就是说,中国那部分先富起来、先富之后再大富起来的人,他们大多拥有炙手可热的权力资源。吴敬链最担心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却不由自主地走向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差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不继续向真正的“市场化”推进,不继续向“法治”经济和“法治”社会推进,就有可能前功尽弃。吴敬链有一段振聋发聩的话,我想摘录下来,作为今天日记的结尾:
“对于当前中国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特性,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愈远,退出的成本就愈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10月21日 阴 星期二
江南雪儿是我在新散文论坛结识的好朋友,她和朱朝敏的散文很吸引我,在论坛里绝对不让须眉。我们仨从此鱼雁往返,谈文论世,每有契合,辄会心一笑。因为不曾见面,故距离产生美,让她们觉得我如何大度包容并有书生意气,言辞间鼓励有加。雪儿在收到《穿着雨衣的拐角》后,在她那著名的博客里写了一段相关文字,继续对昕孺进行鼓励教育。感谢雪儿的厚谊,特转摘她的语录以自勉:
“昕孺,一说他,我就感觉一种亲和加亲切。我认为,他要是国王一定是最有亲和力的国王,他当演员一定是最有人气的明星,并不是刻意,而是来自他内心的积淀与修为。我并没有和他现实接触过,但我们在博客是很近的邻居,我轻轻点击,就知道他的最新动向。所以,从不陌生。他收录在《拐角》一书里的所有诗歌,我几乎都拜读过,现在,这些文字以书的形式呈现,我有久违的重逢感。有些诗歌,再度阅读,仿佛时光回转。无疑,他的诗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拓展。昕孺是中国不可多得的诗人,我希望,他快快变老,最好是满头白发胡子拉碴,这样,在这个按资历说话的国度里,他就能得到应有的厚待。可恨的是,他现在很年轻,离老有很长的距离。我认为,目前为止,他的成就大于他的身份,也许,我没有表达好,也许,他并不在乎这些,但我知道,昕孺,我的朋友,他是大家,事实会证明。”
10月24日 阴 星期五
10月22日一期的《晨报周刊》有关于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一篇文章,叫《国内文学界读不懂勒克莱齐奥》。我得知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获得这一奖项时,也颇感惊讶,因为我从未听说过此人的名头。我没听说过不代表此人不够格获奖,这么重要的奖项如此郑重其事地颁给他,总有它的理由;但克莱齐奥获奖让国际文坛大跌眼镜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既然克莱齐奥属于爆冷,那很多人认为他是冷门也有它的理由。是故,中国社科院现代外国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尚杰先生认为“国内文学界读不懂勒克莱齐奥”便显得较为武断,但不熟悉肯定是真的。
中国作家也好,评论家也好,东西不多,胆子都很大。据说今年的候选人里面仍然有北岛、李锐,据说刘再复先生在继推荐高行健成功之后再次推荐大陆作家阎连科未遂。无论北岛、李锐还是阎连科,即使我们想象,终于把奖颁给了他们,他们是不是就跻身于世界一流作家行列了呢?我看未必。
菲律宾诗人云鹤寄来《世界日报》文艺副刊的样报,上面刊发了我的《五月来临之前》和《月夜》两首诗。令人惊讶的是,报纸是5月13号的,真是远隔重洋啊。2004年赴台北参加两岸诗人研讨会时,我和云鹤住环亚假日大酒店的同一个房间。他后来创办的《东南亚诗刊》在华文诗坛颇有影响。
诗人碧宇从安徽六安县寄来《大别山诗刊》第二期和第三期,这两期分别是六安诗人抗震诗歌专号和全国诗人纪念四川大地震的特刊。我的《黑暗没入光里》、《音乐停止了》刊发在纪念特刊上。这本诗刊还不完全是民间的,其主管单位是县委宣传部,主办单位是县文化局。宣传部和文化局联合起来办一本诗刊,在我的印象中,全国极为少见。六安这个地方,不简单。
10月29日 阴 星期一
茅盾文学奖又出炉了。照例争议一片。获奖的四部书,我没看过一本。所以,无法评说其优劣。但看获奖的几名作家,这个奖项似乎想尽量向艺术性倾斜。这个方向肯定是对的,不像前些年评那么多历史小说,就把玩笑开大了。总的来说,中国当代作家的书谁上谁下都没有关系,连诺奖都像中彩了,何况“矛盾百出”的茅奖呢。但终归是一种奖励,对获奖者应该表示祝贺。
10月30日 阴 星期四
昨晚,湖南师大第三届读书月举行开幕式。这次读书月的一个重要活动是“戴家军”出马,为师大学生做一个有关阅读的系列讲座。戴海老师既是主帅,又当先锋,昨晚开幕式之后,他率先登场。
开幕式非常热烈,鄢朝晖馆长策划和组织得很到位。罗益群馆长我在师大宣传部工作时就认识,他的致辞虽然普通话不太利索,但颇有学术含量。值得一提的是,刘羊、柔止两口子不仅自己来了,刘羊还把母亲带来了。刘羊说,母亲只读了一年书,很想来听听。我当即告诉她,今天听了讲座,就等于是研究生毕业了,您看跳了多少级!
开幕式上,罗馆长给我们(戴老师、鹏飞兄、郑艳和我)四人颁发了“终身读者”的荣誉证书。感谢母校,这是我一生中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高潮当然是戴老师的演讲。讲之前我还为他捏了把汗,有三个原因,一是老头暑假出游身体刚出了点问题,至今未完全恢复;二是毕竟过了古稀之年,他演讲向来是不坐的,怕他吃不消;三是刚才的开幕式时间稍长了点,怕他找不到感觉。哪知老头一上台即是妙语连珠,稿子也不要,娓娓道来时猛然激情澎湃,惹得群情激奋时他忽地悄声细语,台下数百听众笑声不绝,如痴如醉。端的是宝刀不老!演讲完后,同学们拥上来围着他,还要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亲友团几个成员和鄢馆长临时充当“保镖”,一直把他护送到家门口,才放心离去。
10月31日 雨 星期五
昨天下午,晨曦亲自从涉外学院来接我去他们学校。在校园内的桥头堡餐厅共进晚餐后,来到世纪讲坛。我要给同学们做一堂以“诗歌与中国人的生活”为主题的讲座。邓薇带着建海的母亲,还有她的一个同事来了;晨曦和艾青,敏华和阿咪,文培和江冬,都坐在前面为我加油助威。湖南的高校,除了我的母校师大和岳麓书院所在地湖大,我来得最多的就数涉外学院了。我喜欢这所环境优美的学校,喜欢这里充满活力的同学们。所以,当我走上讲坛,看到下面坐满了师生时,心里还略微有点紧张。
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是我第一次站着演讲,而且是站在舞台上,距离听众稍远,在讲的过程中,很难进行互动。而且,讲台是斜着的,我不敢打开矿泉水瓶喝水,怕万一倾倒了水流出来,弄湿讲稿。这样,大概讲了十多分钟以后,我才基本放松,较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11月26日 阴 星期三
龙源网的“昕孺专卖店”在蔡凛立和她同事的辛苦运作下,终于初具规模。最好玩的是,我几乎所有的书都摆在上面(除了尚未出版的《远方的萤光》和早年出版的质量不高的小书),像个琳琅满目的超市。特别是几近绝版的《文画巨人丛书》(一套四本),也好不容易弄了一套放上去。
前天,鄢朝晖师妹派人来提了40本《穿着雨衣的拐角》去,作为师大读书月优秀同学的奖品,感谢母校对我那本小诗集的看重。我又把欧阳白、解、尘子和高山雪鹰等朋友们的诗集送了些给图书馆,也算是添砖加瓦吧。昨晚,鄢馆长来电说,朋友们的赠书证她都放在戴老师那儿了。最令人欣喜的消息是,她从《飞天》1986年第6期上找到了我第一次发表在省级刊物上的那首小诗《小屋子诗人》,并特意复印了下来。感谢师妹的费心费力!
12月2日 晴 星期二
润帝品牌公司的文总和屈总一定要接我到他们公司看看,我就去了。忝居“文化顾问”,不顾不问也是不对的。一去公司,大厅门口就是刻印的《润帝赋》,很气派也很雅致。公司不算大,但人员精干,个个都是一副干事业的样子。吃了饭,文总要我提意见,我就提了三点,一是女员工比例要增加,我向他灌输了美女是先进生产力的理论;二是营销力量要加强,要制订切实而又扎实的营销规划,不能打游击战;三是公司要有分期目标,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目标一定要明确,员工们才知道劲往何处使。
昨天,陈蒲清老师来访。我躬身相迎。老师依然精神矍铄,谈笑风生。我们谈起他的新著《箕子传》,他很谦虚。不过,说到现在中国学术界的麻木与商业化,陈老师慈言中不乏义愤。留他吃饭,他硬是“不麻烦”我们,执意要走。又是一位洞彻人生的老人。
12月7日 阴 星期日
安徽作家项丽敏寄来《金色湖滩》。丽敏是天涯社区散文天下的版主,我经常去那里游览,她是主人,对我们这些冒昧闯入的客人都很热情,让人感到温暖。她的文字清丽敏捷,从容有致,那种味道还不光是读书读出来的。她住在太平湖边上,我十多年前去过,也住过数晚,可惜那时不认识丽敏。
我知道,除了湖光山色,寂寞是那个湖奉献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丽敏说,太平湖的寂寞是一首“蓝调的优柔的诗”。那丽敏就是这样一位诗意生活在湖边的才女。
12月17日 晴 星期三
昨天下午,复生说,想请我带他去师大见戴老师,我求之不得。六点半我和复生到师大,戴老师站在忠烈祠门口等我们。晨报明天在湖大主办一个“鲁迅与教育”的论坛,复生想请戴老师参加后天上午的研讨会。另外,复生邀请了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先生,他想请戴老师今天下午陪刘道玉游书院、爬岳麓山。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当校长时,我正在湖南师大读书,经常听到他的大名,因为他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改革者之一,当时的《中国青年报》对他曾有过整版篇幅的报道。老人现已年近八旬。
晚十点回水木轩。读近期的《晨报周刊》。《晨报周刊》分A、B版,A版是文化版,B版是生活版。我总是只能看看文化版,生活版太时尚,我跟不上。这期文化版上有诗人非牛做的朱健老师的访谈。朱健和彭燕郊同为“七月派”诗人,彭燕郊老师去世后,朱健老师便是硕果仅存了。我编《湖南教育报》副报时,约过朱健老师的稿,后来想做他的专访,不料报纸突然停刊而未遂。他曾多次邀请我去他那里玩,我竟一直没有去打扰过他,我们也就一直没有见过面。我非常喜欢朱健老师的文章,因为经常能读到他的文章,我想,见不见面就是次要的了。祝朱健老师健康、长寿!
12月19日 晴 星期五
这两天的主题是“鲁迅与教育”。上海的鲁迅研究会与《晨报周刊》在湖南大学联合举办这次论坛。我作为嘉宾参加了今天上午的“鲁迅:教育的智慧”研讨会,收获很大。
第一个收获是见到了武汉大学的老校长刘道玉。昨天在论坛上听他演讲,今天在研讨会上听他发言,果然名不虚传。刘道玉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思考振聋发聩。他谈到教育改革的艰难有三个原因,一是以改革代替发展,以改革的伪命题遮蔽现实状况;二是社会改革与教育改革本末倒置;三是革新与习惯存在重大冲突:新的东西即使好也不好,因为不习惯;旧的东西即使不好也好,因为习惯了。
第二个收获是见到了周令飞先生。今天上午,我正好坐在周先生旁边,得以仔细观察周先生的举手投足。我观察周先生意不在周先生,意在鲁迅,因为他是鲁迅的孙子。我试图从他身上努力找寻那个“先生”的身影。令飞先生五官颇像鲁迅,只是棱角没那么分明,但身材比鲁迅高大得多。他的性情通达温润,我想,这肯定是从鲁迅那里遗传下来的基因。人们多看见鲁迅尖锐决绝的一面,看不到他通达温润的一面,所以,无法认识真正的鲁迅。
第三个收获是见到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去年,在湘潭大学召开彭燕郊老师的作品研讨会,组织者便是孟泽。我因故没去,发短信向他告假。后来,我读《彭燕郊文集》,读到孟泽写的序,以为写得很好。不意今天他是半场会议的主持人,我们不仅相谈甚欢,而且得到他的大著《王国维、鲁迅诗学互训》。
今天的研讨会有20多位专家发言。复旦大学张业松博士谈到鲁迅最后被迫用美学来解决现实问题,我是很赞成的。因为鲁迅不是政治家,不是社会活动家,不是慈善家,他只是一名作家。我一直认为《故事新篇》是鲁迅的巅峰之作,是他的绝唱。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位老师提到,鲁迅关注弱势群体,鲁迅作品中“弱者”一词提到40多次。还有一位女士说,鲁迅喜欢“鼻子”这个暗喻,他认为鼻子是人身上最醒目的器官,最容易暴露人的本性,他强烈反对“高鼻子崇拜”。
通过这次论坛,我感到目前鲁迅研究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是鲁迅研究始终在主流文化体系内进行,这就使得鲁迅的怀疑与批判精神流失殆尽,更遑论决绝的姿态了;第二是鲁迅研究的学院派气息太浓,这种研究能培养出教授,却无法造就思想家和行动者。真正意义上的鲁迅研究或许只能寄希望于民间,打着研究鲁迅招牌的纪念馆、教研室和课题项目几近苍白,学者的“深刻”几乎都是陈词滥调,是自鸣得意的八股文。
等所有写了稿子的专家发言完毕,蒙令飞先生所赐,我捡了几分钟做了自己的发言,我说:
我不是专家,我之所以来到这个论坛,一是因为我敬重鲁迅,二是因为我在教育报刊做过20年的记者编辑,我了解教育。
我们现在的教育太危险了!这种教育态势与鲁迅的教育思想和期待是背道而驰的。当年,鲁迅对以社会为主体的教育环境非常严苛,他不惜做出文学上的牺牲,写了大量的杂文,对社会的黑暗与丑恶大加挞伐;但他对受教育者,对学生和弟子则是格外宽厚、包容,他不遗余力地扶持青年作家,他在北师大事件中义无反顾地站在学生一边,等等。然而,我们现在正好相反,我们对受教育者非常严苛,把学生进行军营式管理,让他们夜以继日地大量透支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我们的教育从不考虑孩子的个性,而是不由分说地把个性不同的孩子们放进同一个模子里,让他们模式化、标准化;但我们对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反而格外宽容,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形形色色,都在社会的金光大道上畅通无阻。一百年前,鲁迅呼吁“救救孩子”,砸烂那间围困孩子的铁屋子。一百年后,孩子依然被围困在应试教育的铁屋子里,还有商业时代的黑洞、官本位社会的潜规则等,都在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我们的孩子。
鲁迅把教育堕落的账算在社会环境上,我们却把教育滑坡的账算在孩子们身上。刚才上海鲁迅中学那位老师发言,说现在的孩子不懂得爱,不讲诚信。试问,在一个暴力横行的家庭,在一个父母将所有精力放在麻将和金钱上的家庭,我们怎么让孩子去懂得爱?又试问,在一个坑蒙拐骗事件充斥晚间新闻节目的社会,我们怎么要求孩子来讲诚信?
好比教孩子们仰望星空,我们一个劲地让孩子看天上闪烁的星星,让他看有光亮的东西,让他习惯光明;而鲁迅先生不一样,他大声疾呼,要孩子们看星星周围巨大的虚空,看那厚厚的黑暗。不是说黑暗就一定是腐朽与没落,更重要的是,黑暗背后是无尽的空间,是无穷的可能。我们的孩子,从小以为天上只有几颗星星,他们不习惯黑暗,但当他们碰到黑暗的时候,他们无所适从。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悲哀。
12月22日 阴 星期一
上周六中午,复生要我到河西新民路口的大碗厨饭店聚餐,与席的还有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作家阎真,复旦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张业松,红网博客论坛编辑张亦男。阎真我是第二次见面。办《大学时代》杂志时,郑艳去中南大学对他做采访,他托郑艳签名送了一本《沧浪之水》给我。2006年我去湖南理工学院出差,余三定老师设宴招待,正好遇上阎真在那里讲学,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但人多嘴杂,没说上几句话。这次算是对双方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交代。他问我:“你究竟是哪个名字?把我搞糊涂了。”我就向他汇报了有关我名字的一些故事。阎真与业松聊得很多,他们是同行,有很多东西可以交流。当一名旁观者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来——虽然他们都擅言,但业松是典型的学者,理性严谨,出语端肃;而阎真生动活泼,出语俏皮,童心宛然。
阎真只带了两本书,业松是远来的客人,他自然有一份;亦男是曼妙的女孩子,也自然有一份,剩下我和复生干瞪眼。不像我,一口气带了四本,一人一本。所以,著名作家的做派就是不一样,他永远让市场处于饥渴状态。
12月29日 阴 星期一
上周六上午10点,湖南省诗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湘江风光带的挪亚游轮上召开。谭仲池先生是诗歌委员会主任,他当然要参加;何立伟、阎真、王平、龚政文等虽然不写诗、但与诗脱不了干系的作家们也来了。何立伟戴顶帽子,个头倒显得矮了。阎真几天前刚见过,很是亲切。政文文章好,官也做得好,头上白发多了不少。最潇洒的是王平。很多人不认识王平,王平也不想很多人认识他,但他是长沙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他的文字干净得让你找不出一点渣滓,和他的一张白脸异曲同工。他永远是一副少年的样子,时间拿他没一点办法。他多年不写小说了,手里换了一样更大号的——照相机。很多人都说,长沙的小说家像何立伟、宋元、王平对小说那副懒洋洋的样子,是湖南小说甚至是中国小说的损失。小说拿了他们也没办法,但淡泊使他们在生活上获得了更多的灵气、舒展与自由。
很高兴,还看到了李元洛和彭浩荡老师。彭老师的朗诵总是诗会上最富激情的节目,今天也不例外,但他今天竟然忘词了,他说是平生第一次。朗诵了一辈子诗歌,今天终于填了忘词的空白,真不容易,太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