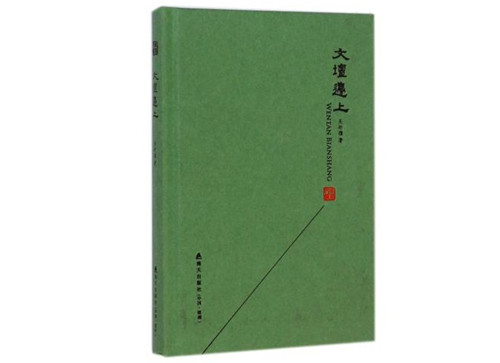
文坛边上·2008年卷
作者丨吴昕孺
5月13日 阴 星期二
周日中午,诗屋论坛和涉外学院的湘流文学社一起举办以“感恩母亲”为主题的诗歌朗诵会。汤文培是朗诵会的总策划。参加的诗人有韦白、远人、定光、雪马、马随、森林伐木、凌峰、海燕、枕戈、殷明等。我第一次与新锐诗人颜觉、周木、多马、李泽清、弥撒、周过等进行交流。涉外的校办主任鞠晨曦与会,他的一段开场白说得很有激情,显露出他的诗人气质。
作为主办者之一的诗屋论坛,欧阳白和我先后上台讲话。我借此机会表达了自己与涉外学院的不解之缘,一是他们的校长张楚廷先生就是我的校长,张校长的教育思想放到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都将是先进的;二是我在主持《大学时代》杂志期间,涉外学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不仅有较为可观的发行量,还成功合作过多次活动。然后,我朗诵了十五行诗《母亲的声音》。
朗诵会很成功,虽然人来得不是很多,但始终在热烈的气氛下进行,有的女生受诗歌和朗诵者的感染,还流下了泪水。涉外学院学生表演的歌舞话剧等节目也体现了这个学校的水平与活力。
5月27日 多云转暴雨 星期二
昨天,岳麓书社紫纯先生通过天涯社区的“留言”告诉我,我的十五行诗《音乐停止了》入选他们出版社编辑的《汶川抗震救灾诗文选》。他在留言中说:“你的诗属于象征派,难懂。”我回答他说:
“紫纯好。看到太多有关地震的诗都是直接抒情,其中固然有让人感动之作,但更多的是抒情太过,没有太大的艺术价值。虽然灾难应该让技巧走开,但既然是写诗,过分抒情对诗歌本身总是一种伤害,就像放油太多的小菜,对健康是有害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更冷峻,更理性一些。写得不好,谢谢您的包容和抬爱。”
这也是我对最近很多救灾诗文的看法。
6月5日 晴 星期四
下午,接到袁复生的短信,说他们将在今晚八点,在新华文图大厦五楼,主办一个有关汶川地震的影像报告会,作品全部由晨报派出的八名摄影记者提供。在会场,见到定光、马随、殷明、弥撒等80后诗人,随后,宋元老师也来了。复生将晨报周刊总编辑龚晓跃先生介绍给宋老师和我,晓跃先生我大约见过三次,他一头长发,清瘦俊秀,下笔如行云流水,才气难挡。《晨报周刊》每期的卷首语均是他的大作,不拘一格,铿锵可读。
报告会以摄影作品为主体,辅以各位摄影师的现场讲述,主标题为《那些悲伤的碎片》。我视力不太好,戴着眼镜也勉为其难,加上前排坐着威武雄壮的作家浮石,看起来比较吃力。总体印象是很不错的,但冲击力没有我预想的强。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平日在网上看了大量的灾区照片,对灾区的惨状已经不陌生了;二是这些照片拍得颇具艺术性,感觉原生态不够,反而削弱了它的冲击力。灾区的相关照片中,令我最受震撼的,是在一个诗友的博客上,看到汶川的河流上漂浮着孩子们的尸体,看上去似乎都是女孩,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好看的衣服。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像是一个枕着一个睡着了……
前不久应朋友之邀写一篇讨论男女两性问题的文章,我写了五千来字,题为《男人与女人》。朋友说文章真好,标题太差,引发不起别人的阅读兴趣。我可能因为长期写诗的缘故,对散文和小说的标题向来不讲究,这一毛病马明博等好友均提出过批评,我也是虚心接受,死不悔改。这回突然心血来潮,既然朋友不满意,我就改为《女人的胳膊与男人的大腿》。他说这个太好了。我亦不以为意。令人意外的是,我把该文发到天涯社区的“散文天下”,不到两天竟有13000多的点击率。我才明白,时下人们的阅读兴趣与欣赏方向是个什么样子。这一方面缘于网络文章多如过江之鲫,标题不醒目,文章立马就会被淹没;另一方面也说明商业社会、快餐时代,连文字也得“灯红酒绿”起来了。
6月28日 晴 星期六
我坐在西藏泽当镇山南地区行署院内某公寓楼二楼,青年诗人陈跃军的书房兼卧房里,努力平息着自己激动的心情,试图回忆这些天来西藏之行的巨大收获。但我知道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我现在依然处于失语状态,或者说,依然处于语无伦次的状态。平时在文字上一贯自信的我,直到到了西藏,才发现自己竟是如此浅陋平庸,语言是如此苍白无力。我不得不承认,要用文字来准确地描述西藏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把这次西藏之行写下来,或许不能道西藏之万一,但我可以肯定,那将是属于我的文字,我自己的文字。
昨晚,跃军和乙乙借着浓浓的酒兴说,他们要在《格桑花开》上做一期我的专号,主题为“一个人的西藏”。我欣然同意,我现在就是一个“藏漂”,我的身体过几天将要回去,我的心灵将永远游荡在这片神奇而神秘的土地上。
7月1日 晴 星期二
昨天,与跃军、乙乙夫妇在山南江城酒店话别,还有跃军的两位朋友沈主任与高主任。然后,跃军送我到车站,又把一条雪白的哈达挂在我的脖子上,并执意给我买上车票。
此时此刻,我竟希望跃军快些离开,否则担心自己会过于动情。跃军现在是最忙的时候,但因为我的到来,耽误了他很多时间,他给我安排得那样周到,自己却很少休息。有这样的好兄弟,夫复何求!
7月5日 晴 星期六
昨天从林芝回来,下午四点到拉萨,诗人李素平开车到八一路接我。开好房后,还帮我买了准备今天上路的一大袋面包,他说是拉萨最好吃的面包。我说,我在西藏、在拉萨享受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风光与最深挚的友情。
晚上,素平兄邀了西藏小说家张祖文和美女编辑汪璐,一起为我饯行。这时接到旅行社通知,五号没有去长沙方向的火车,订的是六号的车票。人不留客天留客啊。情不自禁,加上素平、祖文的“逼压”,喝了点酒,顿时飘飘然如临风而举。醒来已是今早七点,来到宾馆电脑房,草草记之。
7月10日 晴 星期四
昨晚看诗集《穿着雨衣的拐角》的清样。错误不多,只是漏了三篇文章,要补进去。
今天上班,传达室我的信箱满满的。计有《文艺报》冯秋子寄来的6月21日一期样报,发了两首十五行诗:《黑暗没入光里》《有更古老的悲伤吗》。这是古道热肠的散文家周闻道推荐过去的。
还有岳麓书社寄来的样书《五月的殇咏》,是一本纪念抗震救灾的诗文集,收入十五行诗《音乐停止了》。书印得精致,书上镶嵌的黄丝带令人肃然。
《科教新报》6月24日号副刊“麓山夜话”专栏刊发了拙作《我看范美忠》。
7月11日 晴 星期五
还在西藏的时候,西安南阳子就给我来电,《诗选刊》下半月版有一个“诗人地理”专栏,反映一个省的诗人在各个地市的分布情况。下期他们想发湖南诗人的地理分布概况,委托我撰稿。
内蒙读书种子张阿泉寄来四期《清泉部落》。《清泉部落》是一份民办的读书类报纸,每月一期,每期20版,定位为“中国小众读者的观念报纸”。蒙阿泉兄垂青,我还忝居该报“国内执行编委”之职。阿泉就是这样热心肠,只要有机会,就把兄弟们推到前面。读了这四期《清泉部落》,文章皆清爽雅致。如果要说一个毛病,还是长文多了点,与阿泉推行精品短章的想法不是十分吻合。读书文字也弄得很长,不知道这是不是时文的毛病,现在的小说、散文一出手都是鸿篇巨制,但好东西实在少。诗歌稍微好一点,但因为诗歌篇幅小,又被很多人视为文坛的敲门砖。这些严肃的可笑之事,或许是文学走向经典的必由之路吧。
7月25日 晴 星期五
《诗选刊》约的“湖南诗人地图”整理好了,传过去,得到周公度和南阳子的表扬。这是一桩苦差,因为牵涉的诗人太多,拿欧阳白的话说,就是很容易得罪人。为了尽可能全面、客观,我在每个地区找了一个好朋友帮忙,感谢湘潭的吴投文、岳阳的沈念、常德的周碧华、益阳的汤浩、衡阳的郭密林、郴州的杨戈平(解)、娄底的梦天岚、邵阳的尘子、怀化的柴棚、湘西的胡建文等。
8月7日 晴 星期四
南京董宁文寄来《开卷》杂志和他主编的《我的开卷》一书。《我的开卷》收录了我的《<开卷>有益更有情》。
河北衡水收藏家何卫平先生(浅止斋)寄来他担任编委的《衡水古玩城小志》。卫平兄还写了一封信给我,道及编辑这本书的个中甘苦。他和同道一起,利用业余时间为自己城市的古玩城写志,其兴可赏,其志可嘉。
《潇湘晨报》7月31日刊发了拙作《一流文人与三流司机》。他们专为长沙车市弄了一个文人专栏“侃大车”,计有宋元、谢宗玉、王跃文、浮石等人参与。有趣的是,换过好几辆轿车的王跃文想骑自行车,开厌了摩托车的谢宗玉却要买小车了。我就暂且安心坐公交车算了,让他们折腾去,呵呵。
8月28日 雨 星期四
前天下午打球时,熊忠说他奥运会开幕前在汨罗八景住了一个星期,见到了少功老师,老师托他问我好。刚好我正在读老师的大著《暗示》。便给老师去信问安,老师回信告之,他刚从香港讲学回来,八景水库因今年干旱少水,“美景不再,让人十分扫兴”。相信,明年我去的时候,水一定会回来的。八景不能没水呵,没有水,八景的山便会枯涩许多。
9月3日 阴 星期三
前天,领着来长沙出席金鹰节高峰论坛的《安徽文学》主编蒋建伟和《长篇小说》的出品人张荣女士一起去岳麓书院。长沙目前炙手可热的美女作家薛媛媛女士一同前往。我在《安徽文学》今年第1期发表了写岳麓书院的散文《灵魂的入口》,正要送杂志给湖南大学宣传部唐珍名部长。珍名很热情,帮我们办理了免票手续。
岳麓书院是一部大书,我给两位客人一页页翻开,让他们领略里面的精华。薛媛媛表扬我讲解得好。我说,以前一来了客人就找江堤,一边听江堤讲书院,如今斯人已去,我就做了他的衣钵传人。与其说我讲得好,不如说是以前江堤讲得好,我只是听得认真而已。
从书院后门出,过新建的屈子祠,走清枫峡,上爱晚亭;再到麓山寺,直抵云麓宫。小小的岳麓山,以其清新优美,一一向客人呈示儒道佛三教合一而又各据要津的无穷妙意。
中饭后,带建伟和张荣去第一师范参观。张荣喜欢看《恰同学少年》,她特意找到第八班教室,坐在毛泽东曾经坐过的座位上,实地感受了一下伟人的成长。最后一站,是全国第一书市定王台,基本上泡在龙挺兄主持的弘道书店,而恰好在书店碰到了龙挺。龙挺身边的客人是深圳海天出版社的赵浩然先生,他是我1998年出版的一套四本《文画巨人丛书》的发行人。他说,那套书卖得很好,只是目前市场看不清,不敢再版。
昨晚,复生请我到金牛角吃饭,结识了出版集团的苏建科先生和文艺社的崔灿。建科先生是我在师大的师兄,网上叫紫纯,前不久他为岳麓书社编了一本反映地震灾区的诗文集《五月的殇咏》,其中收录拙作《音乐停止了》。在复生主持的《晨报周刊》“20世纪的书”专栏中,我俩都是作者,当然师兄写得更多更好。崔灿则是四卷本《彭燕郊文集》的责任编辑,彭老师生前曾多次提起过他的敬业,今日一见,原是极年轻的一个帅小伙。
9月5日 雨 星期五
我曾经和江堤、彭国梁、王开林、冉云飞等共同写过一本书《21世纪我们做男人》,江堤是组稿人,作者一共有八位,兴致勃勃地把自己当做最优秀的男人搞。书出来好多年,我手头也没有一本了,只好找擅长访书的文培帮忙。人过了四十岁,就想把以前的东西收拢来。与我同一心思的人还不少,这不,接到了故人王道坤从广州打来的电话。他几经颠沛,在南方找到了发展机会,有了自己的工作室,突然想老朋友了,打电话给我,互道款曲,还要去了甘肃柏常青的电话。我还是1991年去过广东的,道坤对我这一不可原谅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并要求整改。
师大图书馆鄢朝晖来电,邀请我十月份去为学生做一堂有关阅读的讲座。问我想讲什么主题,我想起前不久诗人聚会,远人有一个观点我非常赞同,得此启发,我说,那就讲“做一个伟大的阅读者”吧。
9月7日 晴 星期日
昨天上午10点,去芙蓉中路耶士咖啡参加兰心的《一朵灵魂叫兰》签售会。会上,先见了久违的彭见明老师,后与节目主持人罗刚握了下手,再来到诗人们的桌边,计有韦白、路云、李杰波等,令人高兴的是见到了唐兴玲,原来她从广州回娘家住几个月了。
杰波这次给我印象较深。也是第二次见他。第一次是在谭克修主持的麓山诗会上,客套地碰了一下杯,收下他一张名片。昨天,他做东请我们到贺龙体育馆后面的一个小店子吃饭,店名亦颇有趣,叫“茶油香”。杰波一杯白酒下肚,先把在座诗人的诗作批评了一通,然后要服务员拿出一张白纸,要求每位诗人来一句,写连句诗,他起头一句是“秋天来了,叶子黄了”,路云接着写:“那棵树,你跟我站住,站住,站住!”我接着的一句是:“再不站住我就开枪了。”兴玲羞涩,韦白说他从不写这玩意,只好戛然而止。
韦白兄趁着几两酒劲,对我提出了批评,他说的是真心话,我很感激。他认为我评论别人时过于顾忌,过于周全,褒多于贬,显得缺乏自信。我想,确有这个问题,尤其在评论年轻人时我的原则是以鼓励为主,可能有时当老好先生了。但对同龄作家和前辈作家,我还是会尽量做到“以我为主”,以我的阅读理解和美学判断为主,而不会以面子为主。比如,我敬重彭燕郊老师,我也认为他是中国当代最优秀、最富创造力的诗人之一,我完全认同他是中国诗坛“圣徒”的观点,但我不认为他是“世界级大诗人”。因为,我觉得中国还没有世界级的大诗人,彭老师的衰年变法使他脱胎换骨,但晚了一点,天不假年,这不是彭燕郊的悲哀,而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的悲哀。
我认为,彭燕郊老师最好的作品是他的散文诗,《漂瓶》《门里门外》《无色透明的下午》《站台》《混沌初开》等,都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散文诗最优秀的作品。可以说,彭老师是继鲁迅之后,极少几位在散文诗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中国作家。但彭老师的诗歌是令人遗憾的,尤其是80年代以前的大量诗歌,在艺术品质上经不起推敲。有人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我也承认,在那个时代中国不可能出大诗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也许是诗人自己的悲哀,纵有天才,我们亦无力挣脱时代的局限。但恕我直言,只有能够挣脱时代局限的诗人才可称得上世界级的大诗人,这里除了大才,还得有大智、大勇、大胸怀、大气度。
终归而言,中国当代诗坛因为彭燕郊而有了一丝独特的亮色和底气。彭燕郊的意义在于他是一颗种子,他用自己一生的创作经历和诗歌文本告诉广大青年诗歌爱好者:诗人是这样炼成的。这个意义比界定他是一位所谓“世界级大诗人”要重要得多。在我看来,彭燕郊是中国诗歌新世纪的一缕曙光。在这缕曙光的催生下,我们期待看到中国诗歌的太阳。
把彭燕郊推上“神坛”可能对湖南诗歌和湖南诗人有利(一位大师的后面总会拉扯出一些小大师),但对中国诗歌是没有好处的。在文学上,我们应像摒弃诺贝尔情结一样,摒弃“大师情结”。这样说,我绝非反对在全国宣传彭老师,我只是希望湖南乃至全国的青年诗人能真正学到彭老师的精髓,比如他的执著、淡泊和大气,真正做好彭老师的衣钵传人,从而尽快地达到他,超越他。胸怀大志的诗人们,我把一句奥林匹克运动的广告词送给你们:
“喜欢他,就超越他!”这才是对他最大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