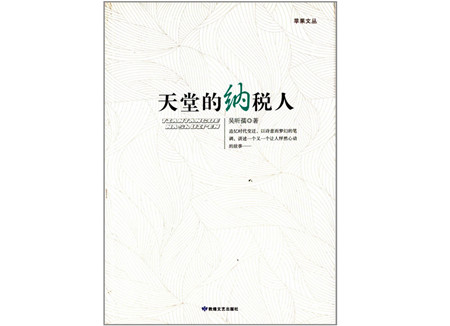
天堂的纳税人(小说集)
作者丨吴昕孺
父亲的钱夹子掉了
父亲丢掉钱夹子的那天下午,天气很诡异。刚吃过午饭,那天中午母亲做的辣椒酸菜特别咸,我扔下饭碗筷子就要喝水,偏偏妹妹也要喝,我们一直共着一个搪瓷缸。
那个搪瓷缸是舅舅去修湘黔铁路带回来的唯一纪念品,上面有个火车头,在两根铁轨上呜呜地开着,头顶上冒的烟像一串挂在屋檐的干辣椒。舅舅从工地上回来,把这只搪瓷缸送给我们。他没有明确说送给我们中的哪一个,最先接过搪瓷缸的是他的姐姐、我们的母亲。但母亲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件纪念品的珍贵价值,她一边和舅舅说话,一边随手将它放在饭桌上。
我早就盯着那只搪瓷缸了,它比剥了皮的冬瓜还白。我还看中了搪瓷缸上那个火车头。我从没见过火车,没想到火车头有点类似于水牛,比水牛还少两只角;但它吐得出像干辣椒一样的烟,水牛吐不出。所以,我猜,如果火车头和水牛打架,可能打个平手。如果遇上宋三毛家里那头经常发疯的水牛,那火车头就不是对手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那只上面有个火车头的搪瓷缸。但紧随母亲之后,第二个拿到这只搪瓷缸的却不是我,而是公认为家里最笨的妹妹。妹妹一顿饭要吃上半天,常挨母亲的打。可这回,当我还在比较火车头与水牛的优劣时,她的手猛然从母亲背后伸出来,逮起那只搪瓷缸,兴奋地绕着舅舅和母亲转圈,嘴里模仿火车发出呜呜的声音。我没有像往常那样,急于去抢妹妹手上的东西。相反,我面露微笑,以欣赏的眼光,看妹妹转圈,仿佛那是一个真的火车头。
我莫明其妙地想着另一个问题,我们从没见过火车,也很少听说过,怎么知道火车的叫声一定是“呜呜”,而不是像水牛那样“嗷嗷”,不是像汽车那样“嘀嘀”,或者像父亲的自行车那样“哐哐”呢?
于是,我深感羞愧,为刚才自己想到的火车叫声竟然与妹妹模仿的相同。我毅然决定改变火车的叫声。我把妹妹叫住,对他说,火车不是你那样叫的?妹妹停下来,拿着搪瓷缸的手收回到胸前,警惕地望着我。
“不是我这样叫的,那是哪样叫的?”她问。
不由分说,在她犹疑的一瞬间,我从她胸前抢过缸子。她没反应过来,两只手仍然在胸前做着拿了一只缸子的样子。我看了好笑,但忍住没笑,因为我怕妹妹哭,她一哭就会坏我大事。
我连忙把她招到一边,诲人不倦地说,火车的叫声像父亲的自行车,应该是“哐哐”叫的。妹妹问,你没见过火车,怎么知道?我恶声恶调地回道,你更没见过火车呢,你连火车的影子都没见过,连火车的屁都没闻过,你怎么知道是“呜呜”叫?
我沉不住气了,对妹妹吼着,我说是哐哐叫就是哐哐叫,由不得你!妹妹既不来哐哐叫,也不来呜呜叫,她用自己独特的尖利哭叫覆盖、勾销了所有声音。母亲听不见舅舅说什么,转过身来呵斥,哭你咯尸!妹妹指着我奋力告状,他抢我的缸子!他抢我的缸子!
这个时候,我总有些心虚,又不甘示弱。我向母亲解释,顺便抵赖:“根本没抢,我在告诉她火车是怎么叫的?”
这句话逗乐了母亲。她说:“火车怎么叫,你们哪里晓得,这个得问舅舅。舅舅刚从铁路上回来,他见过的火车比你们见过的汽车还多。”她露出尘烟之下难得好看的笑,好像舅舅知道火车的叫声是她的骄傲。
舅舅索性把椅子转个身,对着我们,先问妹妹:“你说说看,火车是怎么叫的?”
妹妹嘟起嘴,不做声,一点也不自信的样子。我乐呵呵地等待舅舅叫我回答。谁知舅舅在继续开导妹妹:“其实,刚才我听到你学火车的叫声,很像呢。”我听了心里一跌,一颗石头掉下来砸在自己脚上,痛得钻心。我把一只脚的脚趾竖起来,原地绕匝,像打地洞的小老鼠。妹妹则抬起头来,愤怒控诉:“他讲不像!还抢我的缸子!”
哪里抢了?分明是我先拿的!这句撒赖的话还没出口,舅舅就开始问我了:“那你说说看,火车是怎么叫的?”
这下轮到我不做声了。舅舅又问一遍,妹妹大声代我回答:“他说,火车是‘哐啊哐’那样叫的。”说完,还要指我一下。我狠狠毒了她一眼,她才颇不情愿地把手收回去。
舅舅的总结让我大为意外:“你们两个说的都没错,火车既是呜呜叫,也是哐哐叫的。火车启动的时候,发出呜呜的叫声,意思是,大家注意,我要出发了,可别挡着我的路。火车在行进过程中,发出哐啊哐的叫声,那是它们走路的声音。”
我问:“那么说来,呜呜的叫声是从火车嘴里发出来的,而哐啊哐的叫声是它们的脚步声吗?”
舅舅竖起大拇指:“真聪明,以后你可以去当铁路工程师。火车没有脚,它是靠车轮转动的。”
这下我高兴死了,也不管“铁路工程师”是个啥玩意,举着缸子“哐啊哐”地跑起来。我像个火车头,后面只有妹妹一节车厢,她发出的可不是“哐啊哐”这么优美动听的声音,而是嚎叫。
母亲命令火车停下来。她铁面无私地说:“刚才你们学火车的叫声都对了,这个搪瓷缸也归你们两个共用,不准霸占。谁要是霸占,就剥夺他的使用权。”在母亲奇怪的政策下,我和妹妹就共着一个搪瓷缸喝水了。
有趣的是,自从有了这个搪瓷缸之后,我和妹妹都不记得以前是拿什么东西喝水的了,仿佛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用这个搪瓷缸喝水。
那天中午,我和妹妹同时争着要喝水。妹妹抓住搪瓷缸的手把,我抓住了搪瓷缸的沿口。不要以为我动作比妹妹慢,没有及时抓住手把,而是我根本没抓过手把喝水,我认为那是典型的小孩子的动作,生怕缸子会掉下来似的。我学父亲,从手把的另一个方向,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缸沿,好像不把缸子当回事,仰头将水倒进口中。问题是,我也没比妹妹快,我们几乎同时抓住搪瓷缸的手把和沿口,同时用力将搪瓷缸往自己嘴边上凑。
搪瓷缸被僵持在半空,像飘得极慢的一朵白云。我感觉到缸子里的水在不停地涌荡,仿佛下面有炉很旺的火在将它煮沸。我捏着缸沿的大拇指和食指越来越烫,我想松开,却做不到。妹妹似乎同样如此,她的脸急剧变形、变色,先是像一块慢慢烧红的正方形烙铁,突然好像谁把烙铁浸到水里,密密的头发成了烙铁冒出的一束浓浓的青烟。我只看到她的头发,看不到她的脸了。
接下来,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搪瓷缸里的水像一条龙冲出来,它的头触到了我的鼻尖,尾巴扫着了妹妹的头发,从窗子里一闪而过,不见了踪影。我们还没回过神来,外面天已黑得像砣铁,沉沉地压在山顶、树梢和屋脊上。这时,妹妹恢复了她的五官。我估计,外面那砣铁就是飞出去的龙从她脸上带走的。一带出去就变大了,变成天空那么大,正好搭在山顶、树梢和屋脊上,没砸着我们的头。
父亲和母亲竞相夺门而出,仿佛刚有一个强盗从我家里逃走了。我和妹妹跟着跑出去。的确有东西被抢了,不是我家的,是天上的太阳,刚才它还照得亮晃晃的,一晃再一晃,就没了。我估计,抢走太阳的还是那条龙,它怕我们去追,便可恶地丢下了这砣黑铁。
要下暴雨了。父亲故作淡定地说。
没刮风,没打雷,没闪电,白日如夜,不是好兆头。母亲忧心忡忡。
我和妹妹站在阶基上,望着天。
没有天了,只有无数的乌鸦在飞,它们组成了临时的天空。妹妹鼓起了掌。这个喜欢乌鸦的蠢孩子。父亲回头看她一眼,但没有不悦,他眼睛里似乎装着别的东西,他刚才回头是想把那些东西倒掉,正好倒在妹妹鼓掌的地方。妹妹吓得躲到我身后。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我和妹妹是一对小冤家,一天到晚吵个不停;只要父亲回到家里,我就成了她的保护伞,虽然我根本保护不了她。
好在半个小时后,乌鸦一只都不见了,天重新亮起来。那条龙丢下的黑铁渐渐被阳光融化成水,流进村口的河里。
没戏可看,我们回到屋内。父亲眼神空洞,竟成了对子眼。母亲低下头,露出一副失落的神情。妹妹还在一惊一乍之中,扯着我衣服的后摆,像一只小小的缩头乌龟。我呢,在想那些乌鸦究竟飞到哪里去了,满天的乌鸦啊,难道还有另一块天可以装下它们吗?又在想,阳光是如何把那砣黑铁那么快融化成水的,它怎么没想人都融化成水呢?世界太神奇了。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结论,但我没对任何人说,我怕他们不懂。
再过了约摸十分钟,父亲突然对母亲说,钱夹子找不到了!
我从母亲的脸色知道这一事情的严重性。父亲话音未落,母亲的脸就变成了一张白纸,比剥了皮的冬瓜还白。那种白,我只在舅舅送的搪瓷缸上见识过,当然,现在那只搪瓷缸已经和我一样黑不溜秋了。
那张白纸倏忽飘到我面前,从纸上抖落一句低沉而严厉的问话:“老实跟妈说,你是不是拿了你爸的钱夹子?”
平日我总爱在家里偷东摸西的。比如,母亲藏在衣柜里的月饼、过年熬的油渣、浸在坛子里的酸萝卜,等等。去年母亲买了几斤麻花,悄悄放在碗柜最顶上一格,以为我不知道。母亲的确处心积虑,一来碗柜里除了碗,就是剩饭剩菜,我不感冒;二来碗柜放在厨房,母亲一天有十几个小时在那里忙乎,那里完全是她的地盘。但母亲低估了我对美食的敏感度,我在厨房一转悠,嗅出一种不一般的香味,与厨房混杂着猪潴、油烟和柴火气的日常味道格格不入。
快要过年了,衣柜里没什么东西,我心里便略知一二。待母亲出门去菜地或送一碗猪脚汤去隔壁,我就打开碗柜,再解开顶格上用纸绳捆紧的一个大纸包,哇!里面香喷喷的,是一座诱人的麻花山!我毫不费力地抽出一根麻花放进口袋,立即逃离现场。由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我能做到把纸包扎得和打开前一模一样;而且,我用极富技术含量的手法,小心翼翼抽出最底层的麻花,一点也不惊动上面。这样,底下日益空虚,上面的架子仍然搭着,看上去原封没动,实则早已被釜底抽薪。
纸包不住火。过年了,母亲拿出碗柜里的那个大纸包,一上手就发现重量不对,两手轻轻一按,里面竟然出现大面积塌方。我本来完全有时间跑出去,好奇心按住了我,我想看看母亲的反应,结果她问都没问,扯着我一顿猛打。这是不需要问的,作案特征供出了案犯。在我家里,谁还能如此高智商作案呢?
但更多的时候是,母亲会先进行声色俱厉的盘问,通过我的抵赖或狡辩,前后支离,漏洞百出,形成“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状况,再加以惩罚。这回,难得地出现一次,家里的失物与我完全没有关系,我马上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没拿,钱夹子长什么样我都不晓得!”
母亲没有再问,而是和父亲翻箱倒柜去了。家里从没出现过如此严峻的局面。我也紧张起来,赶紧带着妹妹,和父亲、母亲一起寻找。母亲走过来对我说,父亲的钱夹子是长方形、黑皮子的,课本那么大,里面有两千块钱。
“知道两千块钱是什么概念吗?你爸一个月工资才三十五块六。他工作五年都不得这两千块回来。”
我读书成绩不好,但算术不错,当即纠正:“不对,爸爸五年的工资应该超过两千块。”
母亲大手一抡,作劈下来的姿势:“你不吃饭不穿衣不交学费呵?鬼崽子!”
我抽出所有抽屉,放在地上,一个一个清理。嘴里一边念着,课本那么大,课本那么大……我灵机一动,打开书包,一股脑倒出所有课本,一本书一本书翻,希望能从某本书里掉下一个装着两千块钱的黑色皮夹子。母亲见了没好气地说:“你找个屁啊,我说钱夹子有课本那么大,不是说从课本里能找到钱夹子!”
但母亲的做法和我并没两样。她把衣柜里的衣物全部搬到床上,一件件抖开,看了正面再看反面。忽然掉下来一件东西,母亲大叫一声,捡起一看,却是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封面,红得发黑,上面的主席像阴着脸,好像他也丢了一个钱夹子。父亲听到母亲的叫声,一阵风似地卷过来,看见不是自己的钱夹子,又风一般刮到最里面的卧房,把那间房里的五屉柜掀得嘭嘭直响。本来个子不高的父亲身形更加瘦小,窄窄的额头上挤满了汗珠,好像一群刚出笼的毛绒绒的鸡仔。他的鼻尖上也吊着一颗巨大的汗珠,仿佛是长出来的另一个鼻子。我纳闷,那么大一颗汗珠,怎么不往下掉呢?
父亲的板寸头上沾着蜘蛛网,手上尽是灰。我好奇地到他那间房里去看,那是他和母亲晚上睡觉的地方。一进去我才发现,那间房里十分安静,不仅没人,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能听到其他房间发出的声音。一股阴森的气息攫住了我,让我害怕。父亲到哪里去了呢?他和母亲的卧房是我家的尽头,除了我刚才进房的那张门,没有门通向其他地方,窗户上每隔五公分竖着一根六毛丝,父亲再瘦小,插上翅膀也飞不出去啊。
我怯怯地喊了声:“爸。”
没人应。须臾,响起窸窸窣窣的响动,像土狗子掘土。我倾耳谛听,声音来自床底。正当我俯下身子,要看个究竟时,“扑通”,一个体形硕大的土狗子从床底蹦了出来,落在我的脚边。它抬起黄褐色脑袋,怔怔地看着我,触角上下抖动,像在说着什么。我没管它,依然俯着身子,朝里扫视,床下除了父母用的一个便盆,空无一物。
我跑到母亲身边,哭丧着说:“爸不见了。”
母亲没有我想象的惊慌,她在打开一床旧棉絮。旧棉絮里飞出无数灰尘,灰尘像蛾虫一样聚集在屋内悬空的一注阳光里,看上去仿佛一根长长的金箍棒从窗外伸了进来。我张手去抓。我知道那金箍棒是假的,只能摆看,我想抓一掌那些蛾虫,却一个都没抓到。母亲翻了个底朝天,找出了他们遗失多年的结婚证、父亲五年前获得的“优秀党员”奖状和十斤1962年的全国通用粮票。
我问母亲:“父亲的钱夹子里为什么要装两千块钱?”
“那是学校的公款,取出来修食堂的。”
“钱丢了怎么办?”
“丢了怎么办?找啊!”
“找不到怎么办?”
“找不到会死!”
母亲的脸在阳光下一晃,我看到上面爬满了金色的蛾虫;再一晃,回到阴影中,又全部不见了,只剩下一张不算干净的白纸。
“你爸呢?”母亲问。
“我刚告诉过你,他不见了。”
“他去哪里了?”
“不知道。我看见他进了卧房,卧房里却没人啦。”我没有说,只有一只土狗子。
“莫非大白天见鬼哒,钱夹子丢了,人也丢了。”母亲的焦躁揉皱了脸上那张白纸,我担心它会燃起来。
从一家四口找钱夹子变成了一家三口找父亲。找父亲要简单得多,不需要翻箱倒柜。尽管父亲的钱夹子有课本那么大,可父亲比钱夹子大得多,父亲差不多有老师那么大。我们从没遗失过老师,怎么就把父亲遗失了呢?其实,我们平时见老师的次数要远远多于父亲,一个星期上六天课,我们天天见到老师;可父亲不到周末不会回来,他在七十里开外的一所中学当校长。
不在屋子里。不在屋前屋后。不在菜地。不在后背山上。不在隔壁。天由白亮转为昏黄,由昏黄转为青灰,由青灰转为墨黑,父亲一直不见人影。母亲闷闷地自言自语:“难道回学校去了,应该打声招呼啊!”我不认为父亲回学校去了,因为父亲的自行车还在堂屋里。我总觉得父亲就在家里,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触摸不到它。
那天晚饭,我们吃得稀里糊涂。母亲捧着饭碗,一粒饭也没往嘴里去。筷子把饭拨进去,又滚了出来,仿佛嘴里塞满了东西。我坐在母亲对面,亲眼看到母亲的嘴里是空的。母亲吃饭的情形传染给了我,我试着把饭往嘴里拨的时候,也出现了障碍。明明张开了口,明明舌头主动伸出来接饭,那饭还是一粒粒骨碌碌地往外跑,有的巴结在我的下颏,有的顺着脖子落进我的圆口衣领里,有的直接往地上掉,砸在那些芝麻般大小的蚂蚁头上。
看到蚂蚁,我猛地想起一样东西,心里起了异样的激动。我端着碗,疾步跑到父母的卧房,两只灯笼眼照在地上。房间里没有异样,下午大规模的翻找早已被抹去痕迹,地面也被扫过了。我眼前一黑,下午看见土狗子的地方躺着父亲的一只旧布鞋,很可能是母亲清扫时,扫把从床底下带出来的。我捡起那只布鞋,左边的鞋帮破了,鞋头穿了一个孔,正好大脚趾那么大,里面的鞋垫像一团发臭的酸菜。我把它扔回床底,怯怯地喊了声:“爸。”
马上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声。我循声寻去,在门后墙角找到了那只土狗子。我把饭碗放在地上,捧起它来。它没有跑,反而昂起黄褐色的脑袋看着我。它不大却饱满的头、凸突的双目、前面健壮的双腿,令我肃然起敬,就像平时见到父亲一样。但这时,它落在我的掌心,是那么温驯。它柔软的肚子手感极好,长长的触须挠得我痒痒的。我觉得,它是故意那样,挠我痒是在跟我说话,我们一见面它就说个没停,它说了很多东西。可惜,我一点都不懂。
这时,母亲喊我啦。在使劲喊。她平时就是这样,如果她喊第一声我没有应,下面再喊就会拼尽全力,并把尾音拖得又重又长。我连忙将土狗子匆匆塞进上衣口袋,三扒两撬把饭消灭掉,走到灶房,饭碗筷子往灶上一扔,寻思着怎么处理这只土狗子。想来想去,我决定征用舅舅送的搪瓷缸。那只搪瓷缸有足够的深度和宽度来养这只土狗子,且大小适中,便于搬移和藏匿,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器具了。唯一要做到的是,不能让母亲和妹妹发现,要让她们以为,搪瓷缸莫名其妙不见了。连父亲都不见了,一只搪瓷缸不见,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趁母亲忙着洗碗,妹妹在看一本被撕掉一半的连环画,我迅速拿了搪瓷缸躲进厢房,将口袋里的土狗子掏出来——还好,它活得好好的——放进缸子里。土狗子似乎对这个住处很满意,兴奋地爬来爬去,长长的触角扫在被茶叶染黄的缸壁,发出极细微的沙沙声,仿佛搪瓷缸也在笑着喊痒痒呢。我又丢进去几枚从衣领里抠出来的饭粒,它立即用前脚抱住,一副饥肠辘辘的样子。
我把缸子藏在厢房的西头角落,那儿是家里光线最为阴暗的地方,堆放着几只舍不得丢、却又有些损坏的坛坛罐罐,很少有人去惊动它们。搪瓷缸正好可以放进那只最大的坛子里,以前母亲用它腌酸菜,不幸被我追打一只老鼠时,敲落一片无辜的坛耳,因伤残而不得不退出人民的腌制事业。
为了不露馅,我先下手为强,追着妹妹问,你把搪瓷缸弄到哪儿去了?我要喝水。妹妹满脸委屈地说,我没拿。我愈加大声喝道,最后是你喝的水,快去把缸子找出来!妹妹常常会把强权当做真理,她到处找缸子,找不到,急得哭了起来。我得理不饶人,骂她:“喝水丢缸子,你不会吃过饭连嘴巴都丢掉吧?”
妹妹哭得更厉害,母亲扑过来扇她一巴掌。扇了之后,脸色更难看的是母亲,仿佛那一巴掌扇在她自己脸上。妹妹脸上则像绣了一朵大红花,花刚栽好,她眼里那两只水壶不停地浇水,浇得太多太猛,直到把那朵花浇谢了。
搪瓷缸的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没有了搪瓷缸,我和妹妹不知从哪里找出了以前的喝水工具,一只比搪瓷缸稍小的黄色塑料杯。它对重新得到启用倍感振奋,决心更殷勤、更主动地为这对小兄妹服务,以回报他们的知遇之恩。妹妹在搪瓷缸“丢掉”后第一次用它喝水,它就迫不及待倾杯而出,将妹妹胸前衣服弄湿了一大块,还殃及裤子和鞋子,又讨了母亲一顿好打。
每次吃饭,我故意撒些饭到圆口衣领里,吃完后瞅个空子跑进厢房,反扣上门,把粘在胸口和肚皮上的饭粒捉进搪瓷缸里,让土狗子也能享受一日三餐。我敢肯定,土狗子听得出我的脚步声。我一捧起缸子,它就在里面舞动着触角,表示欢迎;两条粗壮的前腿趴在缸子内壁上,时刻准备抱住掉下来的饭粒;黄褐色的头点来点去,如果我懂它说的话,或许我听到的是一大篇表扬辞。
三天后,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县教育局的,一个是父亲学校的。他们说,父亲有携款潜逃的嫌疑。问母亲,你老公到哪里去了?母亲回答,我不知道,他丢了钱夹子,那里面有两千块钱,他说是学校修食堂用的。我们全家人都在找,找得云里雾里,钱夹子没找着,连他也不见了。他们说,这话说给谁听呢,丢了钱夹子别人信,丢了人谁信?
母亲终于哭了,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哭。我没料到,她哭起来像极了妹妹。妹妹这时却像母亲,冷冷的,不屑一顾,好像事情与她无关。
母亲哭哭啼啼地说,是丢人呢,钱没了,人也没了。我到哪里找钱去,我又到哪里找人去?
那两个人交换一下眼色,这一瞬间天阴郁下来,外面的乌鸦开始集结,树弯下了腰,河流竖立起来……蓦地,其中一个哈哈大笑,原来妹妹躲在后面,挠他的痒痒。他笑的时候,仿佛四面敲起了锣鼓,太阳再次穿破云层,乌鸦见状扑楞楞飞走了。世界恢复了安宁。母亲仍在哭,喧天锣鼓中一抹不和谐的笛音。
那个人还在笑。我不理解那个人为什么会笑那么久,妹妹早已没挠他的痒痒了,她被他怪兽般的笑声吓着,同时也被感染了。几点尴尬得僵硬的笑意在她脸上布控,好像车轮碾过泥水溅到行人的裤脚上。
母亲仍在哭。我能理解她为什么哭这么久。我留神看那个人的口腔,一颗门牙是金的,舌苔肥厚,上鹗有溃疡,咽喉红中发黑,黑中还有一些白色斑点。他注意到我在看他,即刻关上嘴巴,笑声戛然而止,我不觉全身一震。母亲没哭了,仿佛她从未哭过一样。那人对母亲说:“你老公回了,让他赶紧去教育局,不能有丝毫耽搁。”我站在一边想,长大了,我要杀死这个人。母亲点点头,她柔弱得像妹妹,老挨母亲打的妹妹。
母亲整日以泪洗面。那些泪水富含碱性,将母亲丰腴的面庞冲刷成贫瘠之地,一条条沟壑纵横,像刻成的一张棋盘,却已无子可走。母亲从此再也不打妹妹了,她手上没有几两力气,一桶水都提不起。我被迫长大了,做很多大人才会做的事情。我在想,以前父亲一周回来一次,我们见他很少;现在不过是一周一次也不回来了,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有一次,我捧着那个搪瓷缸出神。土狗子依旧在里面舞动着触角,两条粗壮的前腿趴在缸子内壁上,黄褐色的头点来点去……可我没有往日的兴致,我突然很悲伤。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悲伤的感觉。不好受,心里像有一砣黑铁往下沉,身体内部仿佛生长着一个巨大的夜晚,没有月亮和星星,只有无数黑色的鬼脸在变着花样;看不到路,却又在永无止歇地走着,高一脚,低一脚。土狗子似乎意识到了我的悲伤,它不再舞动触角,粗壮的前腿耷拉下来,黄褐色的头僵在那里,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我模拟老师的口吻,轻声然而严厉地对它说:
“你为什么要从床底下跑出来呢?你为什么要被我捉住呢?你为什么要被我养在搪瓷缸里呢?你为什么要成为我的一个秘密呢?”
正当我训斥得起劲,妹妹推门进来。我神思恍惚,忘记反扣门了。我慌忙将搪瓷缸藏到坛子里。来不及了,一切被妹妹看在眼里。自从父亲失踪后,母亲的变化是不再打妹妹了;妹妹的变化是一点也不傻了,反而精灵古怪的;我的变化是,生活中多了这么一点忧伤。妹妹扑过来,大声嚷嚷:
“还说我丢了搪瓷缸,原来是你藏起来了!”
“嘘!”我把左手食指竖在嘴边,右手用力地招呼妹妹,好像她不是自己扑过来,而是我请她过来的。
妹妹看到了土狗子,高兴得跳起来。她把手伸进搪瓷缸里,要去捉它。我先捉住了她的手腕。她生气地说,你不让我玩,我就告诉妈妈!我说,这不能玩的,我们要喂着它。妹妹问,喂着它干什么?我说,喂着它,就是喂着它。妹妹说,你傻呗,喂着它是用来玩的。我说,哥下次捉一只给你玩,这个只能喂着,不能玩。妹妹仰起头,那为什么啊?
没有办法了。妹妹的纠缠让我很不耐烦,却又发不起脾气。我以极快的速度吐出四个字:它是爸爸。
土狗子趴在缸子内壁两条粗壮的前腿仿佛遭到重击,忽然松软下来。黄褐色的头耷拉着,埋在两腿之间。舞动的触角一时僵化在空中,再缓缓落下,像一面巨大的旗帜,遮蔽了外面的阳光。屋子里暗如黑夜,我听到乌鸦的叫声。
妹妹睁大眼睛望着我,她只是吃惊,却未怀疑,这让我增添了底气。我对妹妹说,爸爸丢了钱夹子,怕别人来抓他,他就变成一只土狗子,所以我们要好好喂它,不能让它饿肚子。妹妹说,那赶紧告诉妈妈呀,让妈妈做饭给它吃。我拽着她的手,郑重地说,千万不能告诉妈妈,土狗子不会说话,万一妈妈不信,会把它扔出去,那爸爸就完蛋了。妹妹凑过身子,在我耳边轻轻说,我们一起喂它。
妹妹喂养土狗子比我还精心。她不仅搬来饭粒,还弄些细碎的菜叶,有时甚至能搞到肉末。土狗子特别喜欢吃菜叶,这很像父亲的习惯。它吃得多了,排泄物也多,妹妹每隔两三天要跟它搞一次卫生。她像带孩子一样地带着它。我们很开心,觉得一家四口仍然在这个屋子里,以前父亲每周才回来一次,这样多好,它天天和我们在一起。母亲总是骂我们狼心狗肺,父亲失踪了,还整天笑得像两只红屁股猴子。土狗子让我和妹妹结成了同盟,我们不再为别的事情吵架,我有时忍不住想欺负她,可只要脸一变色或者手一发痒,土狗子长长的触角就挠到我的脸上或手上,让我变得温柔起来。
过了好多好多天,不是十天就是半个月,可能更长的时间。家里又来了两个人,一胖一瘦,却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他们拿出证件,说是公安局的。他们问了母亲很多问题,很多关于父亲的问题。
姓名,年龄,民族,出身,什么时候入团,什么时候入党,什么时候参加工作,在哪里担任什么职务,获过哪些奖励,受过哪些处分,谈过几次恋爱,生过几个孩子,多长时间回家一次,最近有多长时间没回家了,家里有多少人,身体是否健康,有没有家庭遗传病史,有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比如海外关系……
胖子问,瘦子记。胖子和气,瘦子严肃。胖子张开腿,瘦子并拢腿。胖子眼睛大,瘦子眼睛小。胖子抬着头,瘦子低着头。但胖子和瘦子同时站起来,说要到屋里看看。到屋里看之前,胖子先看到了我和妹妹。他走到妹妹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糖,弯下腰问她:
“小姑娘,你爸爸去哪里了?告诉我们,这粒糖就归你了。”
妹妹两只眼睛紧盯着胖子手里的糖,嘴角流出一条清亮的口水。我的心跳到了喉咙口,两只眼睛紧盯着妹妹。她摇摇头,没有去接那糖。
胖子把糖放回口袋,走到我面前,我以为他会问同样的问题。他却径直向厢房和卧房走去,瘦子跟了进去。我和妹妹也跟了进去。
他们察看了所有角落,打开了衣柜,连床底下都俯身看了,只要感觉能够藏住人的地方,他们都进行了搜查。胖子走到厢房里那个堆放坛坛罐罐的地方,仔细瞅了几眼,好在那里明显藏不住人,他们出门又去了杂屋间和猪栏房。家里仅有的一头猪在睡懒觉,对来客爱理不理。胖子看了它几眼,可能觉得不便盘问,没有打扰它。
临走前,胖子回过身来,掏出口袋里那粒糖递给妹妹。
这回,妹妹接了。
我没跟妹妹去争那粒糖,只是问她好不好吃。
妹妹说,真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