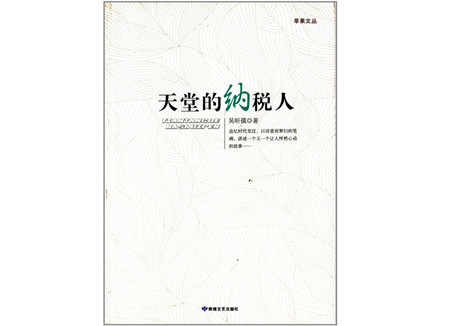
天堂的纳税人(小说集)
作者丨吴昕孺
宝 贝
小玉六岁时,在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她新添了一个弟弟。她当时不知道这件大事有多大,好比爸爸妈妈多跟她买了一样玩具,布娃娃或者生肖狗之类。这一回妈妈从医院里回来,也给她带了一个大玩具,而且这个玩具不需要上电池摁按钮就能发出叫声,还能哭会笑呢,好玩极了。
不久,小玉发现这个玩具好像不是“买”给她的,而是爸爸妈妈自己的玩具。你看,妈妈连班都不去上了,整天在家里抱着他,“宝贝”长“宝贝”短的。这个词小玉没有享用过,他们一直叫她“小玉”,她倒是觉得这个名字挺好听。她原来以为这个名字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她在邻居加加家里玩时,加加的妈妈喊他“加加”,她纳闷地问加加:“你妈妈为什么不叫你小玉呢?小玉的名字多好听呵!”加加比他小一岁,对她唯命是从,但在听到这个问题之后,他呆呆地望着小玉,更加纳闷地摇摇头。小玉为此甚为得意,因为世界上再没有其他人被他们的爸爸妈妈叫“小玉”。现在,她忽然发觉,还有比“小玉”更好听的名字啊,比如“宝贝”,妈妈叫起来像唱歌一样,那可不是一般的歌声,完全不是广播里扯着嗓门唱出的那种杨五六的歌声,而是既有极强的爆发力,又有极强的节奏感,最后绵长的拖腔发射出一股电波,总是电得小玉全身发麻。小玉没明白,妈妈明明是对着弟弟在叫,电波怎么会射到她身上呢?有一次,她趁着摇篮边没人,自己模拟妈妈的腔调对着弟弟那样叫,竟电得她身后电视机柜上的生肖狗一滚,在地上翻了好几个跟头还停不下来。从此,只要妈妈俯下身子,对着摇篮作势那样叫;或者抱着弟弟亲了无数遍,正张开嘴,那一声像爆炒栗子般的“宝贝”要脱口而出时,她就赶紧跑,跑到厨房里,跑到后院猪栏,甚至干脆跑到外面马路上去了。
妈妈的注意力全在她的“宝贝”上,这时候就是来了一伙小偷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搬光她也不会知道。小玉经常巴望家里来这么一伙小偷。她有时闭上眼睛念咒语,念了好一阵,睁开眼睛看到家里的东西都还在,心里很失望。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能让妈妈察觉,否则她就会骂小玉是“神经病”。
爸爸在镇上的砖厂上班。他一回来不管弟弟是睡了还是醒着,不管自己身上尽是灰土,都要去抱他,亲他;以前他可是一回来就把小玉举过头顶,她张开双手,像只小鸟一样在空中飞翔。那是小玉最高兴的时候,比玩玩具还高兴。自从弟弟出生,那样的日子再没有过。她很少哈哈大笑了,很少吃两碗饭了,很少去加加家玩了……她在家里的时候更多了,却更不开心了。
奶奶隔三两天来看一次,也是来看“宝贝”的。有一天,奶奶提着个大包裹急匆匆地过来,小玉和加加在门口玩,她看见奶奶来了,赶紧丢下手里的沙袋,迎上去叫“奶奶”。可奶奶的耳朵被外面的风灌满了,没听见,她跨过门槛,直奔摇篮而去,看着熟睡的婴儿,唤了声“我的孙宝贝”。小玉几乎晕倒。加加喊道,小玉你怎么了?是不是生病了?加加跑进屋里,高声喊道,小玉生病了,小玉生病了!
妈妈终于出来,弯下身子温柔地问她,小玉,哪里不舒服?小玉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她抿住嘴不做声,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妈妈有些着急,小玉,告诉妈妈,是哪里不舒服?小玉看着妈妈,妈妈还是那么温柔、漂亮,还是以前亲热地唤着“小玉”的那个妈妈,她鼻孔里蓦然涌起剧烈的酸疼,酸得她眼泪双流,用手抹一把泪水,却把哭声也抹开了。泪水和哭声小玉都止不住,她对一切已无法控制。她只看到妈妈的嘴一张一合,像在演戏。但妈妈每吐出一个词都被她的泪水和哭声冲走了。她仿佛隔着一面厚厚的玻璃看妈妈,那边妈妈的脸变成了一副凶相,嘴里滚出几颗冲不走的鹅卵石:
“不准哭,会吵醒弟弟!”
奇怪,连小玉自己都控制不住的哭声,妈妈这一喝就止住了,剩下几条泪水的余波在脸上,好像被一锄头砸中的长虫,徒然地翘动着渐渐僵硬的尾巴。
过了几个月,妈妈要上班了。她是罐头厂的工人。任何来她家的客人只要一进门就知道这个屋子里必定有人在罐头厂工作——他的视野里不是罐头,就是吃完了罐头的矮矮胖胖的空瓶子。客厅的墙角摆着堆积如山的空瓶,这些瓶子等小玉的爸爸有空时,便会被全部盛进箩筐里,再挑到罐头厂去,厂里以每只瓶子两毛钱的价格回收。每当销售款回收不及,厂里发不出工资时,妈妈就不得不搬回大量的罐头,这是她工资的物质表现形式。小玉曾好奇地问,妈妈你怎么买回来这么多罐头?妈妈摸着小玉的头,笑着答道,因为小玉喜欢吃啊,小玉是个罐头娃娃呢。小玉是真喜欢吃罐头,她最喜欢橘子罐头和菠萝罐头。她不仅喜欢吃罐头,还喜欢那些吃光罐头后的空瓶子,她有时偷偷把积木丢进里面,再灌满水,号称是她自制的积木罐头。但有一回,小玉心血来潮,她把空瓶子当积木玩,垒着垒着,上面的瓶子跌下来,在地上打得粉碎。小玉觉得做了一件大错事,赶紧用手去抓那些碎片。没想到,那些碎片里面藏了很多血,她一抓,血就涌出来,在她的手心手背像蝎子一样猛爬,蛰得她的小手好痛。血蝎子越来越多,甩都甩不掉,小玉吓得魂不附体,大声哭叫起来。那时她爸爸妈妈上班去了,奶奶在家里带她。但奶奶总是让她自己玩,她和几个婆婆老老在客厅里或者阶基上打麻将。这次事故发生后,小玉便不再玩空罐头瓶子了。妈妈对奶奶的意见一向很大,这次更是互相吵起架来,吵得不可开交,奶奶就回到她老家去了,隔三岔五来看看,从不过夜。
这回,爸爸提出要把奶奶接过来住,妈妈坚决不同意。她说,那不如委托加加的妈妈照看,还上心些;中午我回来喂奶也不会饿着他,有纸尿片隔着又不要担心他撒尿。再说,小玉这么大了,带带弟弟应该没问题。我们小时候,还不是姐姐带着弟弟,哥哥带着妹妹,根本不要父母操很多心。爸爸一听,不吭声了。妈妈上班前,郑重交代小玉:
“一定要照看好弟弟。弟弟是爸爸妈妈的宝贝,也是小玉姐姐的宝贝。他哭的时候就抱抱他,像妈妈那样哄着他;不哭的时候就逗他玩,千万不要喂他吃的东西,他现在只能吃奶,知道吗?遇上你做不好的事情,就喊李阿姨(加加的妈妈)。听清了没有?复述一遍!”
小玉听得挺认真的,她把“宝贝”、“哄他”、“逗他”、“李阿姨”等几个关键词囫囵说过,妈妈满意地点点头,走了。妈妈不会想到,小玉对她刚才那段话其实一点也不服气。她认为,弟弟只是爸爸妈妈的宝贝,不是小玉的宝贝。小玉从没有意识到自己“姐姐”的身份,更不觉得做姐姐有什么好处;反而是弟弟的出生,让她顿时由父母宠爱的明珠变成这个家庭可有可无的人,巨大的失落感催生了她对弟弟的敌意。爸爸妈妈不在家,她又发现她由一个可有可无的人,顿时变成了屋子里至高无上的主宰。她处在权力的真空地带,可以为所欲为地发泄她的敌意。她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一上午,妈妈的宝贝都在摇篮里睡着,像一个横放在超市货架上的瓷娃娃。偶尔他会醒来,嘴里发出咿咿呀呀近似哭的声音,两只小手在空中乱舞。她连忙摇动摇篮,嘴里学着妈妈的“哦哦哦”哼几声,他复沉入梦乡。李阿姨带着加加来看过一次,说了一句小玉好懂事,带弟弟带得好,就走了。加加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看上去他整个人都没他妈妈的屁股大。小玉觉得很奇怪,一个人的屁股可以大到那种程度。
妈妈早早地回来。人还在外面,一股拖长得让人心惊肉跳的“宝贝”电波就开始发射了。强烈的电波吵醒了她的宝贝,没等宝贝哭出声来,一个圆圆的奶头塞进他的嘴里。小玉呆呆地看着,妈妈和她的宝贝融为一体了,像一根黄瓜藤上结出的一个胖黄瓜。妈妈突然没好气地说,发什么呆,快去倒杯水来,我渴死了!小玉走进厨房,从凉壶里倒了一杯水,出来递给妈妈。妈妈喝了一口,皱着眉头问,怎这么凉,你没舀自来水吧?小玉没有回答,她也皱起了眉头,扭头看着墙上那张被撕掉小半边的年历画。妈妈分两口把杯子里的水喝光,有一滴从她嘴与杯子的交汇处溜出来,一路欢畅地往下流,在下巴角悬了好一会还不掉下来。小玉圆瞪着眼,看得实在受不了了,眨巴一下眼睛,再一看,那滴水就不见了,弄得她好生惆怅。
吃完中饭,妈妈又去上班了,这回她似乎去得挺踏实,撒腿就走,没留下大段叮嘱的话。小玉看着妈妈急匆匆的背影,不知怎地,觉得她是那么陌生。弟弟哭了,两只小手在空中乱舞。她连忙过去摇动摇篮,嘴里学着妈妈“哦哦哦”地哼着。但这一招不顶用,弟弟哭得更厉害。他伸出双手,学妈妈的样子用手轻轻拍着弟弟胸口上的被子,弟弟的哭声渐弱;忽而一声尖叫,两只小手使劲舞动,像在抓一只捣乱的蚊子,却怎么也抓不着。小玉不想去叫李阿姨,她情急之下,学妈妈的口型与腔调喊出一声拖长的“宝贝”。真有效,弟弟立马不哭了。哎,这下让他也成了我的“宝贝”。小玉一百二十个不情愿,一边喊宝贝,一边噘着嘴,喊着喊着自己倒成了哭腔。问题是小玉必须不停地喊,她只要一停下来,宝贝的哭声就高高地扬起了,屡试不爽。
小玉很烦。她要对着自己最不喜欢的人不停地喊“宝贝”,仿佛要她对着一个不是自己妈妈的人喊妈妈一样。不过,妈妈现在离她很远了,妈妈和不是妈妈的人没有很大差别。尽管如此,她自己知道,她宁愿不喊自己的妈妈做妈妈,也不愿意喊一个不是自己妈妈的人做妈妈。按照这样的道理,她宁愿不喊任何人做宝贝,也不愿意喊自己不喜欢的人做宝贝。然而现在,不得不喊这个她最不喜欢的家伙做宝贝,她心里堵得慌,撇开他往厨房跑去,用奶瓶灌了一些凉壶里的水,刚走到厨房门口又折回去,把奶瓶里的水倒掉,打开自来水龙头。
水从龙头里流出来,通过奶瓶、奶嘴,流进了弟弟的嘴里。他可能确实是干渴了,吸进几口水后,又呼呼大睡。小玉颇为紧张,这种紧张倒不是害怕,而是对弟弟喝下自来水之后将要发生的情况产生了亢奋与期待。自来水没有烧开的,会有毒吗?弟弟会被毒死吗?她坐立不安,不断地到摇篮边去观察弟弟。他却睡得很好,始终是一个姿势,头歪向右边,露出一边红扑扑的小脸蛋,像成熟的草莓;呼吸是那么均匀,胸脯一起一伏,胜过一件奇妙的乐器。小玉看得入迷,她差点喜欢上这个小玩具了。但她很快说服自己,这是她最不喜欢的家伙,这个家伙简直是她的敌人。
妈妈回来,照例用“宝贝”电波把她的宝贝轰醒,照例第一时间把奶头塞进她宝贝的嘴里。他却意外地不要奶头,吐出来还是哭,妈妈再塞也塞不进去,仿佛那奶头变了味。妈妈感到奇怪,忽地闻到一股气味,她像中了邪似地,以极快的速度扯开宝贝的纸尿片,里面全是嫩黄嫩黄的、流动的秽物。纸尿片扔在地上,把地全部染成了黄色,整个屋子充满了浓浓的异味,臭不臭,酸不酸,又酸又臭。妈妈用了两大盆热水才把宝贝洗干净,这时李阿姨过来了,对妈妈说,你家小玉好乖,带弟弟顶得上一个大人。妈妈说,还乖,带得他拉稀了。李阿姨俯下身,闻了闻说,没事,应该是受了寒,你家宝贝喜欢睡觉,莫放在楼下客厅里,有穿堂风。
第二天,妈妈不要爸爸把摇篮搬到楼下来,就放在楼上卧室里,让小玉看着。不一会,加加过来了。加加想和小玉玩猫捉老鼠的游戏,这是他们经常玩的一个游戏,但最近很少玩了。小玉说,不能玩,会吵醒弟弟。加加板起脸,眼神茫然,伤心伤意。小玉问他,加加你喜欢我弟弟不?加加看着摇篮里,点点头,说,喜欢。小玉再问,要是我不喜欢这家伙,你也喜欢他吗?加加看着小玉,摇摇头,说,不喜欢。小玉说,加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会帮我的忙,是不?这回轮到加加发问了,帮你什么呀?小玉有些想哭,但她忍住了,忍住了加加也看得出来她想哭,加加是个善解人意的孩子。小玉说,我不想要这个弟弟,你能帮忙想办法吗?
加加在旁边的一张小凳上坐下来,以手支头,陷入沉思。他放下手、扬起头时,已俨然成为一个大人。“我有妙计了。”“什么啊,快讲。”“我们把这家伙从窗口推下去,摔死他你不就没有弟弟啦!”“这个办法好是好,可那样他会流好多血的,我不想看见他流好多血。这样吧,我们连着摇篮一起摔下去,他就不会流血了。”
小玉和加加来到摇篮边,他们抬不起这个摇篮。小玉记得他爸爸每次把摇篮搬到楼下时,是拆开来分两次搬的。不久,她发现了摇架和布篮可以分开,他们只要把布篮从摇架上抬出来,然后挪到窗台上,打开窗子,用力一推……
两个好朋友使出吃奶的劲,才把布篮从摇架抬到爸爸妈妈的床上。小玉曾经就是睡在这张大床上,直到妈妈怀了弟弟,她才住到另一间奶奶原来住过的小房间里。布篮搁在床上,一来两个好朋友靠着床沿直喘气,要休息会;二来刚才差点把弟弟弄醒了,得安静下来让他睡深点。过了几分钟,小玉和加加继续把布篮往窗台上移,由于小玉速度太快,加加差点脱手,幸而小玉膝一弯,脚一弓,乘了些力,才让加加重新振作起来。好不容易,布篮底部的一小部分垫到了窗台上。这时,传来李阿姨的声音:
“加加,加加!”
满头大汗的加加只好答应。“在楼上吗?”李阿姨上了楼,打开门,眼前的一幕令她大惊失色。“你们在干什么?怎么能把弟弟搬到窗台上去?太危险啦!玩游戏不能这样玩啊,快放下来!快!”李阿姨三步并作两步,到了窗前,毫不费力地两手搬着布篮放到了摇架上,前后三五秒钟就让小玉和加加半天的努力化为乌有。李阿姨扯着加加的手,勒令加加跟她回去。加加很不情愿,一步一回头;小玉则耷拉着脑袋,功败垂成使她十分懊恼。我要是大人就好了。小玉想。
中午,妈妈和李阿姨一起进屋。李阿姨大声数落着,这两个小化生子玩游戏,把弟弟抱到窗台上去了,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不晓得会出什么大事。你家小玉,胆子真大,以后会是个人物。李阿姨笑得很开心,一边剥着手里的瓜子,把壳呸得到处都是。妈妈的目光刺得小玉全身发抖,她每吐一个字好像扔出一颗石子向女儿头上砸去:
“等你爸回来收拾你!”
小玉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没被石子砸着,她脑瓜子里有一架机器,灵活地躲避着这些打击物;或者她用意念使这些石子在即将砸到她时突然力竭,像羽毛一样纷纷坠地。但在心理上,“等你爸回来收拾你”对小玉构成了三重威胁,一是时间,爸爸傍晚就会下班回来,意思是说,半天之后她将受到惩处;二是人物,爸爸的惩处自然与妈妈不可同日而语,妈妈顶多在嘴上骂几句,爸爸呢?小玉体会过他手的重量;三是程度,“收拾”可不是好玩的,估计不是挨条子,就是要罚跪。如果是罚跪,小玉宁愿挨条子。弟弟满月时,小玉因为不小心撞翻了马上要喂给弟弟的奶瓶,而首次挨了条子;半个月后,她再次撞翻弟弟的奶瓶,爸爸就罚了她的跪。她刚开始抱着侥幸,挨条子多痛啊,跪一下没啥了不起;没料到跪在墙角,爸爸迟迟不让她起来。她浑身像有一万只虫子在爬啊、咬啊,那些虫子进入到她身体的每一个角落,还穿越皮肤爬进了她的五脏六腑,弄得她恨不得立即散架,只想瘫下去,收都收不拢。最是尴尬难熬的时候,偏偏李阿姨推门进来,被她尽收眼底。她嘴里说着要爸爸算了,原谅孩子一次,听口气却并不是那么同情。
“等你爸回来收拾你!”这些羽毛又从地上纷纷扬起,变成一条横幅,悬挂在小玉的左耳和右耳之间。小玉因此出现耳鸣、眼花、鼻血、流口水等种种症状,她决心在爸爸回来之前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以迎接他的“收拾”。但她不知道要做什么,地那么厚,天那么远,做任何事情也惊动不了它们。她呆呆地坐在摇篮旁边的小凳子上,像一只刚完工的木偶;手揉揉眼睛,像一只刚睡醒的蚂蚁。
弟弟哭了。嘴唇干干的。小玉起身,拿了奶瓶去厨房灌凉水。她打开热水瓶,在凉水里掺一点点开水加热的时候,眼睛看到门角弯里一小堆红绿相间的米粒。那是老鼠药。妈妈告诫过她,千万不能吃这些漂亮的米粒,吃了会被毒死去。她看到过不少被毒死的老鼠,硬僵僵的,一点血都不出。是啊,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好主意?加加的主意太馊了,把弟弟摔下去,费那么大力气,还可能让弟弟出很多血。我虽然恨这个家伙,但也不希望他流血,毕竟是我的弟弟呢。
她蹲在厨房的门角弯里,手抓起一小撮米粒凑近鼻子闻了闻,没有别的味道。她吁了一口气,似乎觉得可以放心地将它们盛进奶瓶里。不过是几粒漂亮的米罢了,弟弟吃了它说不定会长得更加胖乎乎呢。她正要把手圈成漏斗状往奶瓶里灌米粒时,一个黑森森的阴影笼罩了她。阴影所产生的强大压力迫使她抬起头来,奶奶!
她战栗地叫道。奶奶伸出满是树皮的手,拧着她的耳朵,往上提。小玉被迫站起,奶瓶掉在地上,水汩汩地流出来,打湿了一些老鼠药。
“这可不是玩游戏,你玩命呢,你弟弟会被你毒死去!”奶奶对着她咆哮,声量却不大,愤怒被舌头裹住了,奶奶的舌头一定在发麻。“我要是告诉你爸爸,他一拳头会把你打得像张纸贴在墙上。”
“下次还这样不?”奶奶厉声斥问。
“不了。”小玉低低地答道,虽细若游丝,却蕴藏着丝丝倔犟。奶奶也降低嗓门说:“只怪你那号娘,放了老鼠药要教你撒,才六岁的妹仔哪里懂得事!哎,作哪门子孽!”
她拿了扫帚,把屋里屋外、屋前屋后的老鼠药悉数清扫,倒到很远很远的树林子里,赶在媳妇下班前回去了。奶奶放了一个纸包在桌上,小玉打开看,全是用旧布剪成的一块块叠得整整齐齐的尿布。奶奶以前也送过同样的尿布,只是妈妈基本上不给弟弟用,弟弟用的全是从超市买来的纸尿片,用一次就包好扔掉,又好看又清爽。小玉很是羡慕,她曾经有拿一块夹在自己裆部、再撒几泡尿的打算,但始终没有实行,因为妈妈对弟弟的纸尿片心中有数,她没空子可钻。
奶奶带来的布尿片吸引了妈妈的注意力,以至于她一晚上都没对爸爸提及上午她和加加的恶作剧。妈妈一个劲地数落奶奶的不是,固执,落后,自私,脾性不好,自己的孙子都不带,等等。爸爸的身子像一个火炉,里面的烈焰把他的面孔烧得铁青,再烧得通红,但火还是被沉默裹着,即便烧得全身发烫,也不露出来。小玉看得清楚,心里却不太明白,她有时上去靠着爸爸,爸爸全身烫得吓人,仿佛擦根火柴能燃起来。
小玉睡不着。她没有在床上翻来覆去,整晚都是一个姿势,仰躺在枕头上,怔怔地看着窗子。窗户上有一团小小的白,像月亮撒的尿。小玉顾不上尿急的月亮,她分析,妈妈今晚是忘记了,如果明天她想起来,肯定会告诉爸爸的,爸爸“收拾”她不过是推迟了一天而已。她在想,她应该怎么办?可是在想出办法之前她就不由自主地滑入了梦乡。
明天很快来到了。爸爸妈妈走后不久,加加神秘兮兮地进来。他一进来就把右手的食指竖在嘴唇中央,蹑手蹑脚来到小玉身边,对着她的耳朵悄悄说:“我找到办法了!”
“什么办法?”
“昨天看电视,那里面有好多人卖小孩。我妈说是‘鬼卖’(拐卖)。我们把你弟弟鬼卖掉多好啊。既不会让他流血,他还可以到别人家做儿子,我们呢,赚钱买棒棒糖吃。”
小玉思忖了一会,说:“把弟弟卖掉,爸爸会不会打我?”
加加漫不经心地说:“没卖你弟弟的时候,你爸爸也打你啊,大不了多挨一顿打呗,多分给你一些棒棒糖就是。”
小玉说:“是啊。没卖弟弟的时候,他经常打我;把弟弟卖了,就只打最后一次了。以后我就是爸爸妈妈的宝贝。我们赶紧把这家伙抱出去卖掉吧。”
加加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你要答应我,赚钱买了棒棒糖,分给我一半。如果你挨了你爸的打,我再多给你十个。”
小玉说:“没问题。我抱人,你叫卖。我们得走远点,最好是去汽车站,那边人多,好卖些。”
小玉用一块床沿巾包好弟弟,抱进怀里。加加则猫着腰走在前面,看到他妈妈不在门口,手势一打,两个好朋友迅疾出了屋门,向小镇南面的汽车站奔去。路上碰到一个貌似熟人的妇女,热情地跟小玉打招呼:“小玉,抱着弟弟去哪里?太阳好大,莫晒坏弟弟了。”小玉信口呼应了一声,继续向前冲。
到了汽车站,人确实很多。小玉机警地四周望望,没看见一个面熟的,他们仿佛来到了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加加拍着一个提旅行袋的叔叔的手,问他:“你买孩子不?我们只要一百个棒棒糖的钱。”叔叔满脸狐疑,他大概压根儿不相信加加的话,用略带恼怒的眼神看着他,甩开他的手,走到一边去了。
小玉轻声对加加说:“一百个棒棒糖是不是便宜了?”
这时,加加看准了一个头戴毛线帽、穿着牛仔短裙的女子,他放大了声音问道:“阿姨,你要不要孩子?我们想把这个孩子换两百个棒棒糖的钱。”女子诧异地张大嘴巴,她来到小玉身边,揭开蒙着弟弟脸部的床沿巾,用手指刮了刮弟弟的脸,说了句“好漂亮的小家伙”,便径直去了车站办公室。
不一会,两个穿制服的中年男子过来了。他们问小玉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问加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问小玉抱着的孩子是谁?抱着他出来干什么……天阴了,原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把小玉和加加重重包围起来,连太阳都看不到了。
小玉和加加被带到了车站办公室。弟弟可能被一系列事件惊醒,高声哭叫起来。小玉抱着他,学妈妈的样,一边摇晃身子,一边嘴里“哦哦哦”地安慰他。但他还是哭,哭叫声越来越大。直到小玉的爸爸妈妈和李阿姨都来到车站,妈妈一把从小玉怀里抱过孩子,孩子不哭了,妈妈却放肆痛哭起来,哭得肩头一耸一耸,像一座即将坍塌的山。爸爸手里拿着一根粗大的木棍,正欲对着小玉劈将下去。妈妈一手抱着她的宝贝,一手死死拽住丈夫的手臂,哭泣着哀求道:“不要打她,求求你,不要打她,求求你……”好多人都上来劝,有人将爸爸手里的木棍抢走了。
好,故事暂且打住,不能再啰唆了。要为读者朋友揭开的谜底是,小玉是我,我就是小玉。后面发生过什么事情,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大概我和加加跟着爸爸妈妈和李阿姨回家了,家里看上去没有变化,爸爸妈妈继续喊他们的儿子做“宝贝”,只是他们终于决定把奶奶接过来带弟弟,把我送进了学前班,一年后我进入村小学启蒙,成为一名学生。除我之外的其他人都感到意外——我的成绩一直很好,上高中前我总是班上第一名。
我再没有对弟弟起过歹心,和加加的关系也渐渐疏远,反而加加和弟弟后来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晃二十多年了,我在复读一年之后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毕业接着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2006年,我公费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去年回国到母校湖南师范大学任教,是湖南第一位拥有国际执照的心理咨询师。我弟弟初中没毕业死活不去读书了,只好跟着爸爸到镇上的砖厂做事,每天一身泥土也乐此不疲。有趣的是,现在砖厂的厂长不是别人,正是加加呢。
上个月回去参加弟弟的婚礼。爸爸妈妈的笑脸好像滚水泡的米花,开心得不得了。晚上闹过洞房,我们围炉而坐,一起聊天。我谈起小时候我想弄死弟弟的事,爸爸妈妈矢口否认。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那时可乖了。我们在外边做事,你还不到六岁,把弟弟带得几多好,隔壁李阿姨直夸你。”我说:“那时我多么想你们像喊弟弟一样,喊我一声‘宝贝’啊。”爸爸和妈妈对望了一眼,没做声,妈妈拿着火钳在土围炉里倒腾,柴有些湿,没有燃,妈妈弯着身子吹了一口,一股浓烟呛得她泪水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