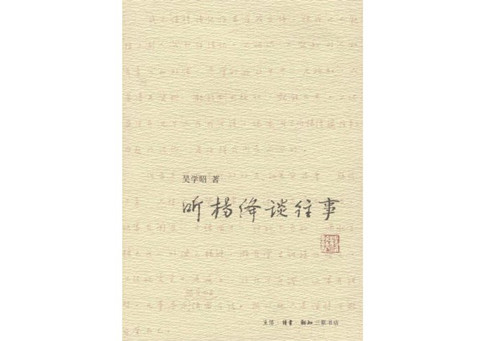
一辈子的妻子、情人、朋友
——读《听杨绛谈往事》笔札
文丨奉荣梅
曾经看到评选 “中国最美的书”的消息。获得这一称号的书的共同特点,是追求简约、流畅、轻盈,注重回归图书的本体功能,彰显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完美结合。于我而言,在一年有限的阅读中,心目中最美的书不仅是装帧的精美,内容的厚重可读才是衡量的标尺。
三联书店出版的《听杨绛谈往事》,可说是那个读书年我心目中最美的书。书封的材料与颜色都是“最美的书”追求的简约风格,草黄褶皱的书封,杨绛清雅的手写书名和手稿影印衬底,充满柔性之美、书卷之气。传主杨绛在序言中自谦为“平常人”,说“我不值得传记作者为我立传”,但作为有家学的知心好友、吴宓的女儿吴学昭写传,她应承了。于是,我陆续地花了十来天时间,每天于青灯下,细细阅读这近三十万字的传记,犹如旁听着当年近百岁的杨绛与同样是名门之后的吴学昭,一起叙谈重温近一个世纪的往事,体味旧情。
杨绛先生归结自己,“平生做过各种职业,家庭教师、代课先生、中学教员、小学教员、灶下婢(大家庭儿媳妇也是一项)、大学教授、研究员。经验只有一条,我永远在群众中。”在别人的眼中,杨绛一辈子是站在钱锺书身后的女人。其实,在文学创作上钱杨一直是比肩而行的。还可以说,杨比钱出名更早。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是她创作力十分旺盛、佳作迭出的时期,《小阳春》等小说和许多清新隽永的散文,大多写于这段时期。杨绛本名杨季康。1942年冬天,杨季康在上海北区小学上课,在写剧本的李健吾、陈麟瑞的鼓动下,尝试写剧本。第一部四幕喜剧《称心如意》,以故事悬念丛生、环环相扣,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生动活泼,被著名导演黄佐临看重,演出大获成功。当时杨季康不敢用真名,随手取笔名“杨绛”,一夜间杨季康成了“杨绛”,而且一直使用到今天。接着她还写了三部喜剧《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和一部悲剧《风絮》。杨绛出名后,被剧团当成了贵宾,剧艺界很欢迎她。一次钱杨同去看戏,作者热情招呼杨绛,却没怎么搭理钱锺书,钱锺书心里窝囊,他回家后就发牢骚不再陪杨绛看戏了。当时,钱锺书刚回上海教书,偷闲写短篇小说,已于1941年出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写在人生边上》,他便说:“我也要写,我想写长篇小说!”从来都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的杨绛,为支持钱锺书,让他减少授课钟点,不请女佣减少开支,自己兼任灶下婢。一位大家闺秀、千金小姐,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实在难得;外面名气那么大,在家什么粗活都干,于是杨绛被钱家婶婶称赞: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
抗战胜利后,钱锺书一下扬眉吐气了,杨降退居其后成了“钱夫人”了。钱锺书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1946年任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被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参与编辑《英国文化丛书》,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人 ·鬼· 兽》。同年,《围城》完成,在《文艺复兴》上连载,很惹人注意,都在打听作者是谁,有人说,钱锺书就是杨绛丈夫。次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连续两年再版,为钱引来了大量fans,可怜的杨绛愣是被fans认为是“孙柔嘉”。——读到这,我不由笑出了声。其时,杨绛正受聘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授,创作翻译一些作品,写了不少散文,她的讽刺幽默不像钱锺书那样尖刻辛辣,却也含蓄中听,同样动人。
两位同样幽默风趣、妙语传神,同样清醒忍韧的人,六十年的相携而行,纵是千般艰辛,也一样不失生活的情趣,钱锺书称杨绛为“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作为钱夫人的才女杨绛,应是最幸福的女人了。
可是自解放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间,除了文论,杨绛没有创作一篇文学作品。钱先生也一样,在解放后的十七年中,也没再进行文学创作。“文革”结束后,杨绛很勤奋,创作了《“大笑话”》、《“玉人”》《鬼》、《事业》等多篇小说和各具特色的散文,她自己最满意的是《干校六记》和长篇小说《洗澡》,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另外,不大为人知的,杨绛还是个外国文学翻译家,她精通英文、法语,还自学了西班牙语。她在教书闲暇,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小说,将英译的西班牙名著《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翻译成中文《小癞子》,活泼开朗、富有幽默感的她,凭她欧洲文学名著的丰富知识,以传神的笔调,译文生动流畅。她也是个好学而认真的翻译者,后又对照法译本重新译一遍。再后来,她自学西班牙语后,又从西班牙原文再译一遍。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作为国内首部从西班牙文翻译的中译本,不仅被国内译界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七十余万册,而且还得到西班牙方面的赞誉,杨绛也因为翻译该书的贡献而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

传记中,最让人深味的是杨绛智慧的人生体味。在每一个阶段,她都一些妙语归结——
“抗战期间,最深刻的体会是吃苦孕育智慧,磨炼人品。后来在单位被轻视,被排挤,披上隐身衣,一切含忍,也是抗战时练下的功夫。”
1951年秋冬的“三反”思想改造运动中,杨绛在“洗澡”中被一不认识的女生揭发遭受屈辱,后亲见化学家高崇熙、留美园艺家虞先生的自尽,她“且把这番屈辱,当成一种锤炼,增强自己的韧劲儿,否则往后遇上更严厉的批判甚至斗争,又怎么经受得住?”
钱杨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愿放弃自己的文化信仰,不愿过问政治。钱锺书对社会政治极度清醒,对人间世态洞悉洞察,多少年来,他保持缄默,不做颂圣诗,不做歌德式表态,从不贸然就政治发表意见。杨绛也是“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披上‘隐身衣’,乖乖地不闻不问”,悠闲地观察世事人情和自己的内心,更深入、更真切地体味人的本性。文革中她被剃“阴阳头”、大会批斗、戴高帽“游街”、下干校……不管处境如何,读书和工作始终是他们的最大乐趣。杨绛从未失去她的幽默感和同情心,相信人性,始终以她锐利的眼光和敏感,在观察这被颠倒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切。
读传至此,我便想起了几年月前在著名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家采访时,有幸亲睹了钱锺书、杨绛夫妇与钟叔河及夫人朱纯的书信,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共四十几封。其中2007年1月26日一封,是96岁杨绛在得知朱纯去世的消息后,以娟秀的蝇头小楷,工整细密地写了两页信笺,安慰钟叔河先生。其中写到:“同是未亡人,你有女儿两双外孙四个,我则是‘绝代佳人’了”、“她比我的女儿福气多,你也比我的福气多”、“希望她在病中还想到过我,也希望你不复脆弱,且在‘老头’的书房里与书为伴吧。”信中一种悲凉之气袭来,但仍是一腔对文友的同情和安慰,不乏幽默。
正如吴学昭的感慨:“杨绛确是一个特殊的人,病弱的身体、忙碌的家务、悲凉的心境,都未能阻止她提笔写作。”我还先后读着杨绛先生的《我们仨》(2003年)、《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2007年)。幽默淘气而充满情趣的钱先生,生动活泼多才多艺嗜书好学的女儿钱瑗相继离她而去了,她一边整理钱锺书的旧作,96岁时她开始讨论哲学、探索人生的价值(生)和灵魂的去向(死),细心地为自己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今年的七月,杨绛先生迎来104岁生日,身体依旧很好,仍然思路清晰、精神矍铄。“沉定简洁的语言,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又渗入诙谐幽默,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
杨绛先生的文字功力,也显示了她一个多世纪从容坚忍的人生态度: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本文刊发于《雨花》2016年02期)